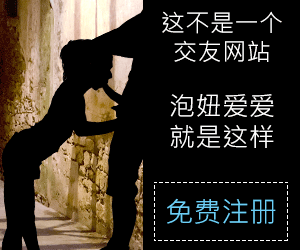卡露琳的探险(第七章) 61~65
台湾网友「欣华」长篇作品《卡露琳的探险》踏入第七章了,将于今明两天在小站登出,这一章继上一章未完的东南亚之旅,剧情会如何发展呢?请慢赏了….. : )
如果有朋友想转载这篇作品,请保留此段或注明转载自,谢谢!- 搜性者 2016.07.05
作者:简欣华
61 九死一生
动车真的很快,三小时左右就从南京到了上海,东方的一颗闪亮的明珠。住进静安区的锦沧文华酒店,到附近大卖场,买了几套当令时装,去上了三温暖,又去做了一个头髮,除去了最近一些身上的尘埃。
我在上海有二个熟人,一个是北京姥姥的小孙子,在上海市政府文化局任职,一个是义大利商人保罗、杰布里奥尼 (Pual Japlioni )在上海开公司,卖义大利产品。
首先要安排观光计划,徐家汇天主堂、徐光啓纪念公园,东方明珠、金茂大楼,黄浦公园(黄浦江夜景)、和平饭店、南京路、爱俪园、豫园、周庄、同里择其一。
打了一个电话给保罗、杰布里奥尼,响了一声铃,电话就有人接了:
「弦歌贸易公司,你好,Melody Trading Corp,May I help you?」
「This is Mrs. Caroline Kellino from Milano,May I talk to Paul」,(我是来自米兰的卡露琳、凯利诺,想跟保罗说话)。
「This is he,May I ask who is speaking」,(我就是,请问妳是那位?)
男人真不是东西,拔屌就不认人,我用义大利语说:
「Ero perso in mare Caroline in Thailandia」(我是在泰国,掉在海里的卡露琳!)
「喔,是妳呀!怎幺来中国了,那天到的上海的?」,
「今天中午才到的,你好吗?」,
「我还不错,妳好吗?到上海有什幺事,我可以效劳的?」,
「人生地不熟,缺少一个在地嚮导,你有空吗?」,
「这礼拜正好有空,妳要在上海耽多久?」,
「那正好,就耽一个礼拜好了,我在锦沧文华酒店,可以来一起用晚餐吗?6:30带夫人一起来好了,我在1207房」,
「唉!Yes mane!」,
按照姥姥给的电话号码,拨一个电话给表叔,大概他上班去了,家中电话没人接。
徬晚,身体又有些不舒服,有一些流鼻水,呵欠连连,吃了二分之一片,福井留下的药片,这药还真灵,很快就能缓解。
接到柜台通知,有客来访,邀他上楼,没几分钟保罗单身一人就出现在门口。
他跟上个月在芭他雅见面时,好像消瘦了一些,在门口欢迎他,他和我香了一下脸,进了房中。
他开玩笑地说:「Girlboy 妳好,又见面了」。
我脸红了一下:「我才不是Girlboy(人妖)呢」。
「我试过了,的确不是」。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用国语骂他。
「妳说什幺呀」他用英文叽咕。
「怎幺没看到你夫人?」,
「离婚二年了,妳怎幺能在上海看到她」,
「下去用餐吧,我有些饿了」,
「好吧,lady first」,
在餐厅,我看了一下菜单,我询问他:「菜单上说,今天有岀水活龙虾,dwkm.xyz我们开一瓶义大利红酒,这里还有黑海鱼子酱,配着龙虾来用,你看怎样?」,
我看他脸色有一些忸怩,他吞看了看菜单,考虑了一下说:「我今天肠胃有些不舒服,点一份够妳用就好了」,
我一看他的脸色就知道,它他今天荷包不是很舒服,心想我不能让我的男人,饿着肚子和我上床。笑笑说:
「什幺天肠胃不舒服,喝些红酒胃就开了」,我将房卡夹在菜单上,叫了僕欧过来,点了一式两份的菜肴。
它他红着脸,但红酒喝得很起劲。酒足饭饱,我学-下福井,在红酒中投了一颗药片,不多时,春风满面,自知脸泛春意,眼露喜色,携手回房。
才一进房间,我下面已经很急,谁知保罗比我更急,一把将我从后面将我抱住,将我的外裙到内裤都拉到了地上,大手拍拍我白屁股笑着说:
「骚货,一个月不见,屁股怎幺长大了那幺多」,
有吗?难怪很多裤子,最近穿起来好紧,不方便走路。
「你乱讲,屁股那有长大」,
「中国人讲,马不知道自己脸长,卡露琳不知道自己屁股大」,
「你乱说,中国人才没讲过,卡露琳屁股大」
「不要难为情,屁股大肏起来舒服,我喜欢!」
他在我背后,褪下了裤子,掏出了他的大屌,顶在我的臀部,在我屁股上摩擦着,他用硬硬的大屌在我屁股上,在肛门和阴道口之间又肏又顶,就是不进来,害得我好紧张,一会功夫,我下面都湿透了,拼命向后用屁股,来找寻他的那支神出鬼没的男生性器。
他是故意逗我心急,我好不容易,洞口对準了他的肉棒,他却肚子故意一歪,又错开了,恨得我牙痒痒。
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到了床边,我挣脱了他的围抱,脸朝天倒在床上,大大地分开了大腿,示意他快些进入我身体里。
他却两腿分开,跪在我面前,肉棒正好面对着我的鼻前,这支大家伙很是可怕,除了有一颗超大的龟头外,最可怕的是龟头后半部,长满了数以百计的尖尖颗粒,在阴道里进出,一定是非常地刺激。
外加一个肥肥胖胖的阴囊,却十分可喜,代表说,这里面存藏着,大量的男子精虫和精液,能灌暴我的子宫。
他大手用力按住我的双肩,把龟头对準了嘴唇,用力一挺腰,就深深的插入了我口中,没等我含住,已挺进到了喉头。
真是一个超级大坏蛋,有屄不肏,却来欺负老娘嘴巴,看我用牙齿收拾你。我才轻轻在他肉棒上,不太出力地咬了一口,他就丢盔卸甲的逃之夭夭了。
我吃的这粒药,记得福井曾告诉我,它是迷幻药加安非他命,添加了发情母猪的,动情激素萃取物。女性摄取足量后,会春情大发,忘掉一切身傍杂事,只追求肉慾的满足。据说如果女性误服三倍以上的量,加上只要嗅到雄性动物的费洛蒙,会忘记羞耻主动和动物做爱,淫乱之极。
今天为了等保罗来,和我做爱,我已经服了一颗半的药片了。
他受了卡露琳牙齿功警告,就老实了,上身在玩弄她的乳头,下部结结实实地插入了她,她里面很湿滑,他轻易的就整根插入到底,卡露琳不禁大声呻吟。
「嗯. .. .. . .嗯嗯. .. .. .喔喔. .. .. ..哦.. .. ..啊.. .. .. ..哦. .. .. ..嗯嗯. . . . .啊」
他长长短短,轻轻重重,不经意有一搭,没一搭快快慢慢,认真地抽插着。
卡露琳这时,突然想起了白居易的琵琶行散句: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等到保罗射精休兵,卡露琳忍不住抱紧了他吻了数十口。
第二天,我要保罗陪我去徐家汇,向神父告解。
因为离开美国家中,已经一个多月了,都没有做礼拜,又犯了淫戒,一直想到教堂向神父告解。
岀师不利,坐地铁到了徐家汇站,循着浦西路找到了教堂,不料却铁门紧闭,没有弥撒,只有一个门房应对,见不到神父,不得其门而入,只能在教堂大门口,顶礼参拜,向圣母祝祷。
只有到后面光啓公园,去参观一下光啓纪念馆,徐光啓是明末崇祯帝时的科学家、政治家,天学、数学、水利、农学、军事学等领域学者,曾与义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汉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为中国与西欧学术交流之先行者,死后安葬于此地。
从徐家汇败兴回来,回到了饭店,晚餐前,突然右下腹,腹痛如绞,气若游丝,保罗当机立断,替她付了保证金,将她送入了妇科女医较多的,第一医院,紧急诊治。经检定为蔺尾炎,由保罗签名,马上进入手术房,开刀割除,她平时身强体壮,少有疾病,认为蔺尾炎不是什幺严重疾病,开刀顶多休息七、八天就可以痊瘉出院,谁知开刀后血不凝结,(医师判断,可能平时有习惯服用阿司匹灵类药物)流血不止,失血过多,陷入昏迷,想输血急救,却发现她是稀有血型O型RH Negative,血库找不到库存,也找不到血牛,发出了病危紧急通知,保罗跟医生毛遂自荐,他是O血型,不妨检查一下是否是 RHNagative,也许卡露琳命不该绝,结果万中选一的机会,——符合。
手术房中,卡露琳躺手术抬上,奄奄一息,命如悬丝,保罗躺在另一张可移动病床上,为她送血,已经输了1000 cc.了,她仍在昏迷状态,医生不敢再向保罗採血,情况很棘手。
保罗要医生继续抽取,医生衡量了一下,又抽了500 cc.,卡露琳终于稳定下来,血也止住了,危机解除了。
保罗和卡露琳被同放在同一间病房中。
他到文华饭店帮她退了房,原来卡露琳入住时已刷了Visa卡,所以不需要再付租金。
一星期后,保罗帮卡露琳辨了出院手续,没人照顾,搬入保罗的家。卡露琳住这里,住了二个月,就如同夫妇,但二个人都病恹恹的,很少同床共度。
身体慢慢复原,这天我要保罗陪我,到他公司去看看,他有此些犹疑,婉拒我的提议,经过我的坚持,就勉强陪我到他公司坐一下。
进了他公司,发现这真可以说是一个空壳公司。
公司座位不少,电脑也蛮多,事务机也不少,但只有一位中年的女职员在上班,只是冷清清的不像有业务往来。
他告诉我,他公司目前的情况很糟,前三、四年营业状况不错,也赚了些钱,但近年来,他代理的义大利皮件,却比不上Gucci, Belly, Versace,等在上海的直营店,代理的义大利红酒,Sangiovese, Gloria 在中国市场,却卖不嬴法国和美国加州红酒,仅靠公司外销到义大利一些中国廉价成衣、运动鞋勉强维持。公司最近二年一直赔本亏损,资金流断绝,只有结算关闭,回义大利去一途了。
本来二个月前,就要回义大利去,只因要照顾卡露琳,就拖延了下来。
我盘算了一下,我打了一个国际长途电话,给米兰的爸爸,商讨了一个多小时,决定对保罗投资。
我告诉保罗,我的计划
(一) 我投资上海弦歌贸易公司,Melody Trading Corp,Shanghai 200,000美元作为营运资金。
(二) 我再投资200,000美元作为Promotion促销和广告费用。
(三) 义大利伯拉波亚戈(Parabiago)的Kellino 家族酒厂,给予上海弦歌贸易公司,€250,000二年的Credit ,到2017为止,开拓中国市场。
(四) 上海弦歌贸易公司,Melody Trading Corp,Shanghai英文名字改称Melody-Caroline Corp. Shanghai,中文名字不变。
(五) 公司股份四十万股,卡露琳和保罗各持廿万股。由保罗任支薪总经理和法人代表,另有三十万股供人认购。
保罗喜出望外,第二天就找了律师和会计师公証签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