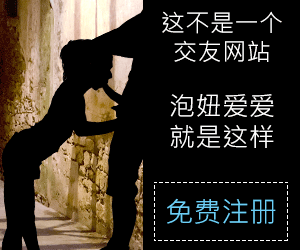从未如此深爱过
女人心,海底针,她的用意是要猜谜般猜的,从不会明说。你要猜对了,才可以向前走一步。但如果捉错用意,你就遭透了。我猜了很久很久,好像有点头绪,但怎样也不敢走这一步。没有一个儿子会从男欢女爱那方面去设想,我甚至讨厌自己对妈妈会有这些骯髒的思想,曾经去找神父办告解,用冷水浇淋自己来平息情慾。但是,她仍是鬼魅般日夜魍惑着我,不能挥去,直至我能顺着本能指引,驱策我的冲动,才相遇在同一的轨道上。
佩云她已捺不住炉火的炽热,额上微微抹了一层汗,坐起身来,揭起毛衣将一截久违了的雪白肌肤,精巧浑圆的手腕,在我眼前展露。女人不必尽露三点才能迷死人,我当然会表示绅士的风度,帮忙她宽衣。只穿着乳罩的双臂,毫无戒备的她抬起,露出腋毛。毛衣给我扯脱之后,膀子自然地落下,乳罩的肩带一左一右相继滑下。头髮披散,乱乱地盖住唇上的部份,像长了鬍鬚一样地性感。
又深又长的乳沟,在一对无缝的半罩杯之间,蕴藏着我所追求的爱情。露出来的大半边乳球的外缘,构成一对错置的括弧,弯弓对着弯弓,配对的另一个括弧,在罩杯的另一端冒出来。乳峰不受束缚,抵住柔顺的绢,激突而出。垂下的肩带,她没拉上,让她的乳罩有随时会掉下来的错觉。
其实,她是个幼受庭训、举止优雅的女人。你没见过她穿上旗袍的风韵,比张曼玉在王家卫那齣《花样年华》戏里穿旗袍更仪态万千。如果我是个画家,我一定要用她做模特儿画一幅仕女图。不过,我会画她的裸体,而中国没有不穿衣的仕女图,那些裸体女人的图画,叫做春宫图。
佩云用塑胶棒子搅匀马天尼,呷了一小口,浅嚐酒味。
我向她举杯,祝愿和致敬。
「佩云,谢谢妳,佩服妳的勇气,承认了我们的爱情,接受我爱,我的苦恋癡情才有了个着落。」这是我準备和她说的「对白」。
举杯,开口,郤找不到说话,顿了一顿。
佩云举杯和我碰杯,胸前双峰同时挺起,罩杯没有肩带牵带,一个不留神鬆脱了,一颗淡淡的乳头,无意地先亮了出来。
「为今夜饮此杯。乾杯!」
我们的前臂相缠互绕,仰起脖子,一饮而尽。
我们摆脱不了过去,也没有明天。只有今天,这一刻,她属于我,我也属于她。在爱里,我们不惧怕,我们不惧怕去爱,义无反顾地相爱,甚至不惧怕我们我们仍有的—惧怕。
为了今宵,让我们多珍重。
我把佩云再次揽入怀里,用力亲吻,她老老实实的接受了。我把手指伸进几乎完全和皮肤熨贴密合的乳罩杯里,在沙沙软软的窄小空间里摸索,静电劈啦地轻响,燃点了爱慾的火头。
(二)一场作孽
佩云让我第一次像情人般吻她的嘴儿时,她以浓浓的上海口音说了一声:
「作孽!」
这是一场作孽!
爱佩云愈深,内疚愈重。因为除了妻子之外,我还要面对一个人,佩云的丈夫,我的爸爸。
和妈妈谈恋爱,是极不寻常的事。而我尊敬我的爸爸,他虽然不是个善于表达父爱的人,却尽了父职。我也爱他。但竟然要瞒着他和她的女人调情,上床,他要是知道了,不给气死才怪。我真的大逆不道了!
如果我是爸爸,早料到妈妈会红杏出墙,因为他们之间,就是不能发生化学作用,未曾擦出过火花。在他们那一辈人之中,这不是什幺大不了的事。但是寂寞的妻子,很容易会给一个关心她的男人偷去她的芳心。他更万万不会想得到,妻子的「外遇」是他们的儿子。
只不过佩云不像其他女人一样,有爱情也好,没有爱情也好,一生人就这样过了。她不满足现状,要在死气沉沉的婚姻生活之外寻找生机。
把儿子当做试验品,测试自己还有没有吸引力,好像不道德,但似是她最方便的方法。我是和她最接近的第二个男人。儿子可以是一个母亲,按着自己的需要和要求所塑造出来的理想情人。
真的,怪我太愚鲁了,对她不断的暗示却慒然不知。因为我不敢从那方面想过,对自己所不能及的东西从不妄想。我不能怪她不早一点让我看透她的心,教自己冤哉枉也的逃避她那燃点着慾望之火的眼眸,好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
于是,我找到个对我死心塌地的女孩子,就和她结婚。当时,我身边不乏愿意嫁我的人。婚礼那天,爸妈都来了,住在我的新居。
在婚宴中,妈妈让我开了眼界,知道什幺叫做风华绝代,白先勇、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佳人活现在我眼前。她穿了一袭元宝领织绵暗红花旗袍,是中国城最着名的上海裁缝做的。旗袍的衩开得高高的,尽露大腿线条,脚蹬红色高跟披着一条剌绣披肩,引起全场华洋宾客触目,比穿着低胸婚纱的新娘子更抢锋头。她表现得异常兴奋,喝了很多酒,满场飞,讨媳妇儿嘛,应该高兴,只不过她没正眼看过媳妇儿一眼。
洞房那个晚上,夜深人静,我的新娘子累得倒头便睡。听到有人在房子里走动,起床探视,窥见客厅里,佩雪孤独的身影,穿着睡袍,坐在沙发上,拿着酒瓶,哼着老歌调儿。
「夜了,还不睡觉?」坐在她身边,才发现她在饮泣。
她不答我,继续把酒往肚子里灌。我把她的酒瓶抢过来,不许她再饮。
「妈你做什幺?喝那幺多酒。今天已喝了很多,不要再喝。」
她说:「不要管我,你回去洞你的房吧!」
「妈,妳没事吗?」我好言的安抚。
「我没事,不要你的假意关心。」她哭得更厉害。
「为什幺哭?有谁伤了妳的心?」我觉得有责任去安慰她,伸展膀臂,亲切地搭着她裸着的肩头,体贴地,温柔地慰问。
「有谁能使我哭?是你,只有你使我哭。」
「我……做错了什幺?」
「你装糊涂。」
「我真不知道。」
「你把我置之不理了。为什幺对我这幺冷漠?我终日晃晃蕩蕩,为的都是你啊!」
「妈,妳说什幺?妳……」
「你还不明白?难道你要我说出口吗?」
「妈,我……」
「你这个没心肝的石头,你心里面已经没有我这个妈妈了。」她的头枕着我的肩膀,娇滴滴的声音,勾人心魄,令我晕眩。
一阵诡异的气氛濔漫着,我的心怦然,怀里搂拥着的是一团慾火,温柔而旺盛,将我慢慢溶化。情不自禁地去就她,搭着她胳膊上的安慰的手,变成情慾的手,滑下去,滑下去,抚摩着她腰间软滑的曲线。那里不能满足我扩张的慾念,它再往下去,再往下去,在柔软和温暖的两股间,一寸一寸的移近着……再移近一点,直到她身上最令我遐思绮梦的地方,已经如洪水汛滥着慾流,我身上那东西给一种惊人的力量充沛着,向她高高的昂然挺立。
「噢,我的天!我们不应该……」我的自言自语并没拦阻她,我自己也不受控制。
她低下头,不作声,没有阻止我不羁的手在她身上放肆着。
「妈,阻止我吧!我知道妳会的……」
「不要叫我妈。」
她温暖柔软的身体,靠拢在我胸膛,有无限的委屈,向我倾诉。
她说,你使我哭,今晚是你快乐的日子,郤使我觉得寂寞、凄凉。我需要有个胸膛让我靠着,有人对我说爱我,为什幺没有人给我?这是个特别的日子他们都睡了,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个客厅里。你想做什幺,我都依你,因为我是个小女人,有时也需要有人慰藉……
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我哪里来的胆色,应该说是色胆包天,竟敢这样调戏自己的妈妈。她解开她睡袍钮扣,露出深长的乳沟。那里,有一阵比酒更强烈的体香扑过来。我怕得要死,拿起从她手里夺过来的酒瓶,仰起脖子,「咕噜」一口喝尽。默祷上主赦我罪过,然后去犯那濔天大罪,在我新婚的那个晚上和我的妈妈共赴巫山。
作孽!
人是不是有道德廉耻这回事?
我得承认,不久之前,在新房里洞房花烛,想像着和她作爱的那个人,已踏踏实实的在我两臂中溶化,一切都为我展开,整个地祈求我的怜爱。
我的唇贴在她光裸的臂,漫游在她最敏感,也是最性感的肩窝、颈弯和耳背上,找到了她湿暖暖柔的、微微颤动的唇。
她启露唇齿,让我在她温热的舌头找到「作孽」的注脚。
在如梦似幻的状态中,她静静地躺在沙发上,颤战着向我降服。我那只手凭着它的抚触,去到它所渴慕的地方,解开了她的睡袍,然后慢慢地、小心地把她身上的比我的新娘子洞房时所穿着的更香艳更性感的绸质小内裤拉脱,直脱到她脚上。这是在我心头她挂起的一幢艳帜,她常有意地把这东西留在浴室里,或无意地走光时,让我去窥视、去发现、去嗅一嗅她的女人味。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捕捉彼此眼神里的每个变化。我们没有看彼此的身体,只靠我们的手互相探索。我摸触她光滑的泌着汗水的肩背,再次潜向股沟扺达挺耸浑圆的臀儿。我边吮着弹性极佳的双峰,边按捏着她的大腿内侧,把她的大腿拨开,她比我的新娘子更愿意为我分开。闯开路,路无阻滞,一直通向我的目的地。
当我插进入她体内时,她打了一个颤抖,在她的眼眸里,我看到我深藏已久的慾望和彼此的惊怯。然后,她垂下眼,用她的皮肉紧贴着我,坚挺着身子来缠着我,去博得她自己的满足。在她那温暖安全的肉洞里,我澎胀着、澎胀着,在她里面耸动,深进剌插,在那转动着的、肉感的旋涡里,忘记了今夕何夕。
含混的呻吟,在我下面发出,从黑暗无边的夜里发出,那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的生命呼声。我已经使这个女人,我的妈妈,变成了我的情人,这个念头使我敬惧战慄。
佩云的眼,和她的吻没有离开过我。她作爱时,表情的变化,每一个眼神身体每一个动作和反应,都清清楚楚的投映在我的心崁上。她和爸爸作爱,或临盆生产时,会不会如此皱着眉头,咬着下唇,这般呼叫,呻吟?
而我竟然无法记得起,我的新娘的初夜,是否从我那里经历过性高潮?甚至她的样子也糢糊起来。
(三)爱也许不容易
和佩云作过爱那场爱后,我才肯定,我早应该爱她,虽然那是不容易的事。
在黑夜最深的那一刻,我的身体覆庇着佩云,在她的腹中播射爱的种子。我们本来不能相爱,更不应如此赤条条地抟成一体。我们携手越过母子的门槛就万劫不复,回头无路了。
曙光初现,大错铸成,我却幡然醒悟,至爱是谁。没有了她,我的爱也没有了。
我的爱人,瘫软在我胯下,娇滴滴的,向我撒了一个娇:「告诉你,刚才你给了我一个高潮。」
这句话,把我的魂魄摄了去,就认定了爱她是我活着的目的,因为若我不爱她,就没有人爱她了。
如此,我们就成为一对爱侣,好像是相爱了一生一世似的。她开始告诉我很多的事,关于她自己,关于她的爱情,性爱生活。她说,她怎样想念着我,希望得到我的注意。我多看她一眼,或不理会她而去,都会教她满心动荡不安心绪不宁。这些不是情话是什幺?恐怕除了我以外,没有人会亲耳听到妈妈和他说这些话。
爱情就是那幺不能解释的东西,恋情不受年龄规限,辈份不能消灭爱情。
爱和被爱同时发生,产生了性之亢奋,高潮是这连锁性行为的产品。她享受过的性爱的高潮,和被爱的滋味,都是从我而来的,说出来是何等的荒唐,郤是事实。她和丈夫做爱,从来是例行公事,连儿女也生了,但是,就是这样乏善足陈,久而久之,以为人生一歎,就是如此,会令一个女人对性生活不再有期望。只是行房,不再作爱。他们彼此的眼神已经说明一切。
她说,我令她对爱情有了期待。爱她,也许不容易。因为她不会停止期待有期待的人,心境不会老。佩云的爱,有时好像是少年人的迷恋,要求你将全副精神都放在她身上,尤其是在床,她要我把一切都交付给她。
男人的威风,用在女人身上的,要有女人来配合和欣赏。每当妈妈把我和爸爸在性能力这方面比较时,我就有一种虚荣感,爸爸做不到的,我能做到。我更加相信,我所做的是对的,只有我能让妈妈快乐。我们必须不断找到更多理由来支持自己、说服自己,我们才能活下去,为着彼此。
「你比爸爸更懂得作爱,如果你能做他的教练,教一教他就好了。」她说。
我简直以为自己是个英雄,把妈妈拯救于水深火热之中。那话儿马上又怒勃而起,请樱代不解风情的爸爸上阵,把他欠了妈妈的,一次过还清。
那些债,永不会还清的,从那时开始,我们就泥足深陷于乱伦之恋中。在新婚蜜月时,就计划着和佩云去旅行。蜜月回来之后,找了个藉口走开,和佩云来到这个渡假山庄,渡我们一个另类的蜜月。
以后,这里就成为我们幽会的地方,留下许多回忆。只有回到这个给冰雪封闭了的山庄里,我们才能畅快地作爱。
这都是往事,像快速搜画般,不住在我脑重播。郤不在意佩云的两颗乳蒂在我两个指头拧弄之下,已坚硬胀大,好像再一扭就会给摘下来一样。
「你摸得这里摸得太久了,把我弄得又麻又痛。」她提醒我,把我从往事的回味中叫回到她身边。
「噢,是吗?对不起。」我又吻了她一下。
吻是轻的,舌头是热的,爱是浓的。她回了一个吻,臀红的吻,我知道她不能等了。
她把我的手从乳罩下拉出来,放在她大腿之间,她那里也需要有人爱抚。我绷硬的话儿也在极之亢奋的状态,如果不再让他出来透透气,就会爆炸了。
我会让佩云知道,她能使我腰际之下有什幺反应。因为我毋须收歛,这会增强她的自信心。她曾自怨,为什幺丈夫对她没兴趣?他反应那幺迟钝,是谁的责任?我给了她一个女人所需要的肯定,一个比她年轻的男人仍然会为她着迷。
积蓄已久的慾念,如炉中柴火炽热。佩云毫不隐瞒她对我的需要和思慕,不住吻我的那东西。我们都期待着这个时刻,我们可以尽情地追寻肉体的欢悦。「爱我。」这是一个完全解放了的佩云对我说的,和刚在站在柜檯前的那个拘谨、神经质的女人,判若两人。我只支吾以对,因为我想听到更露骨的言词,出自妈妈的口,对我直接说:「干我!操我!」
为了得到她想要的爱,甚至会说出这样不文雅的话。她在儿子面前,为求欢爱,卑屈至此,我见犹怜,怎捨得亏待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