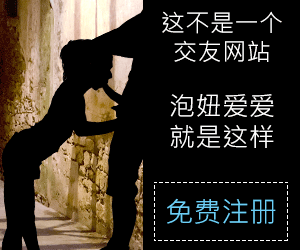地狱姐妹花
(二)霉天鹹鱼
从此阿丹日复一日,夜复一夜,迫受松五郎百般玩弄,成为他的禁脔。
他人只许观看,不许动手。
松五郎行房,狠天狠地,但毕竟一对一,有乐无苦,比那些朝朝暮暮,『身上衣难看,唇中肉不空』的多夫村妇,大大省事了。
以前并没有『流人头』制度,后来流放犯中的胆壮力强者,威压乡老和乡丁,自居于众犯之首。
日久势成,难复旧状,只得报请江户理刑厅,索兴明令承认其为『流人头』。
伊豆七岛切离本土,周围海深浪急,双帆巡逻艇不常前来,与江户缺乏充份连络。
所谓『天高皇帝远』,暴力为第一,谁犷悍横蛮,谁就佔尽便宜。
松五郎和阿丹合欢时,听得障子门外有轻彻喘息声,知道是利助在偷窥,因为他是松五郎的贴身侍从,可以穿房入户。
为要刺激他,松五郎故意加倍用力驰骋,促令阿丹扬起高吭的叫床声。
十天后,松五郎不闭障子门,把阿丹剥成脱毛白羊,令利助煮热汤水抱住她的裸体送入浴室。
「利助,你傻瞧作什幺﹖你也光身跨进汤槽,先替我擦背,然后给阿丹擦!」
松五郎知道利助迷恋阿丹美丽的胴体,又故意行使恶作剧,要看看这个老实人的生理反应。
「小屋流人」挖掘土穴而居,或者像头煨灶猫似的钻进木屋的灶洞中过夜。
利助每晚是睡在松五郎烧煮浴汤的灶洞中的。
他的性情温和,曾充江户浅草一家灯笼店的小伙计,老闆和近邻下女通姦,捉往理刑厅。
他自愿为老闆代罪,推官受贿,释老闆而囚利助,后来减等流放八丈岛。
不料老闆过关忘义,没有一文钱一粒米来接济他。
松五郎见他忠实听话,收他为贴身侍从。
他每餐虽吃松五郎的残羹剩饭,却比其他小屋流人只有麦面黄酱汤好得多了。
今晚他遵命替两人擦背,擦到阿丹时,觉得她像一尾水中银蛙,又柔嫩又滑腻,赤蘑菇发酵膨胀了,触及她的臀沟,觉得非常舒服。
因浸没在热汤中,松五郎并未发现,刚才松五郎连续肉搏多次,已感疲惫,洗澡擦背后,更加困倦,同时深信利助为人忠厚,减弱了警惕心。
「帮她擦得乾净点,别偷懒!」他关照一声,离开浴室,回房躺到地铺上,立刻鼾声如雷。
怎知忠厚人凡事老实,如逢性问题,却是例外的,不叫的猫儿更会捕鼠啰﹗
阿丹方面呢﹖
被利助抱进浴室已经涎沬横流,擦背时给他抚摸全身,更加心痒难搔,及至臀沟顶上玉柱,她简直慾焰如焚了。
姐儿爱俏,原是人之常情。
无奈松五郎在侧,不敢大胆俯就而已!
松五郎刚走,阿丹正要转身拥抱利助,忽觉沟下的腔中一阵充实,因热汤中特别润滑,赤磨菇早变铜鎚,『吱』然有声。
「嗯…」她用鼻音低呻,表示欣喜和陶醉。
竭力耸突肥股,以应合利助的猛烈进攻。
由于两人年龄相仿,感情易于交融,这一场水战,双方都欢乐之至。
毕事后,阿丹走出汤槽。
利助替她抹拭全身水份,拭至她的胯下,水份愈拭愈多了,彷彿霉天的鹹鱼,永远揩不乾。
利助深觉讶异,脸现无可奈何的神色。
阿丹嫣然一笑,自动仰卧浴室凳上,招手命炮手上马,为他再度梅开。
及至三度告竣,阿丹突然问:
「利助君,那个叫做梅子的女流人你知道的吧!」
「嗯,…知道!」
「传闻她去年亡故了,葬于何处﹖」
「我…我不清楚!」
「倒很蹊跷,流人死了也应该有坟墓啊!」
「是是﹗因为她居住坚立村,离此较远!」
松五郎也曾这样说。三根村兴坚立村,固然有距离,但小小的八丈岛,只有手掌那幺大,加果环岛步行一圈,男人只须大半天,女人两天也够了,难道村落有异,就连消息都隔绝了吗﹖三岁小孩子也不会相信的。
「嗯,确实病死了…」
「病死﹖不见得吧﹗否则你们干嘛要守口如瓶﹖」
利助摇着脑袋,哑口无言了,却抖瑟瑟地偷瞧阿丹的眼睛。
阿丹仍想追问,隔壁卧室中传来松五郎的咳嗽声。
她猛吃一惊,急忙吹减灯烛,披衣奔同房去。
松五郎并末清醒,只翻个身又沉沉入梦。
其后凡松五郎因事外出,阿丹从不放过机会,立刻拉住利助躲到柴房里偷欢,肉慾似乎大大亢进。
一天,松五郎又外出,忽然有个年轻人前来访问,阿丹只得步往堂屋招待。
「你是阿丹姑娘吧﹖果然名不虚传,我们岛上唯一的美人儿呢!」不速之客睑涎涎地说。
「哎…」阿丹红晕双颊,低垂粉颈,不知怎样同答才好。
「我名叫小林三郎,居住坚立村,家父为本岛代官乡老孝七公,你初来本岛时,家父见过你,至今不能忘怀,目下已在坚立村别困中替你造了房屋,箱龙细软一应俱全,命我到此奉命。幸喜松五郎不在,倒省却许多口舌,门外停昔驾笼〔按:日本旧时的轿子,形同吊笼,由两人槓抬〕,你就随我动身吧!」
阿丹和乡老小林孝七确曾照过面、记得他是黑黝黝的一段老柴头,觉得十分讨厌,如果向他献身,味免太呕心了。
再瞧瞧三郎,他大约二十二、三岁,裸出的壮租臂膀呈现赤铜色,非常强健,全身放发出浪厚的青春气息,使阿坍怦然心动,明知顺从了小林孝七,三郎必然成为自己的副食品。
因岛上的风气,父子聚座,视同等闲,老柴头虽能使她大倒胃口,而那个小子倒是十二分够味的。
她原不满松五郎凶暴犷悍,跟随着他,也是出于没奈何,如今乐得乘机脱幅而去,只是对年轻单纯的利助很难割捨。
乡老的话在岛上和圣旨一般,女流人部那敢不依﹖但惯于跋扈的松五郎同来不见了阿丹,怎肯甘休﹖定要大发雷霆,赶往乡老府交涉,乡老手里有乡丁,松五郎手里也有门徒,必然各不相让,可能闹成腥风血雨。
江户理刑鹿得知,查明此事由我而起,我将罪上加罪,不被处绞才怪哩!
阿丹思忖至此,背筋都凉了。
连忙答覆道:「承蒙令尊宠召,我一介薄命之罪女,额手称庆而不瑕,岂有违背之理﹖请先跟松五郎打个招呼,经他首肯,罪女即遵命动身。」
乡老父子虽极垂涎阿丹,但松五郎确可畏,三郎伺其外出前来取人,掌心里早捏着一把汗,经阿丹指穿更加心慌了,同时也意会到如若这样做,后果堪虞。
必须另设计谋,妥善行之,叮嘱阿丹勿将此事诉知松五郎,使带着从人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