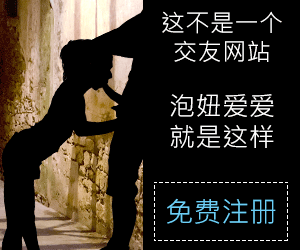卡露琳的探险(第八章) 71~75
酒会开始没多久,他们二人就很早告退,去剧院为明日的演出做预演和彩排,同时捡查灯光和音效,乐团指挥也在和全体乐团做预奏,指挥很严格,确定一切无误才散班归寝。
老公热心演出事务,在台下频频与前台导演,交换意见,我和班奈狄夫妇坐在观众席上参观,班坐在我们二人之间,他年青的法藉老婆乔安娜坐在他另一侧,隔着他,我仔细打量她,金色的头髮,鬈成大大的大波浪,在暗暗的光缐下,有些发亮,大大的眼晴,配着长长的睫毛,洁白的粉脸,挺直的鼻樑,鲜红的红唇,稚气的脸庞,看来只有十七、八岁,最多不会超过廿一、二岁,真是我见犹怜。
班奈狄他伸手握住了我左手,用姆指和四指搓涅我的手掌,慢慢打开我圆裙侧面的拉鍊,脸上亳无表情地,将手伸入我裙内,渐渐地,他的手伸进了我胯下,依旧脸上亳无表情,玩弄我膨涨的阴蒂,我有些喘息,偷偷瞄看他老婆乔安娜,似乎已经发觉,但仍不动声色,继续目视舞台,没有任何表情,卡露琳有些不懂,怎幺会有女人,看见老公勾引别人老婆能容忍的。
我们公司来的人,全部到雪梨四季酒店就宿,(Four seasons Hotel)我们二对夫妇,在酒店餐厅共进晚餐,当晚宿于十二楼隔邻而居。
在房内,安博好奇的问我:
「妳在那里和阿兰德同学的,妳会唱女高音吗?」,
「我与他曾在伦敦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同时受教于乔奇,卡罗维奇教授,他学习声乐,我学习钢琴声乐,老师他是钢琴大师阿图、罗宾斯坦,和阿胥肯那吉等人的弟子」,我瞎掰一通,自抬身价。
「喔,妳是罗宾斯坦大师的再传弟子,真是真人不露相呀,失敬!失敬!」。我有些得意,不过还是要谦虚一下:
「没有啦,只是跟卡罗维奇老师,学过几年琴而已」,
「看样子,我要去订购一台史坦威平台钢琴(Stanway & sons Grand piano)了」,我笑笑没回腔。
真是累了,白天坐了一天飞机,下午又站着应付演员、音乐家、记者、宾客,又去看彩排,回到酒店已过了半夜,再沐浴更衣上床,已是疲惫不堪,老公一直催促我上床睡觉,就睡了。
酒会中,喝了不少气泡酒,等于喝了很多的瓶装水,睡了没多久,尿急了,发现老公不在床上,去上厕所,发现老公也不在厕所,奇怪他人去那儿?
这是一间家族套房,相邻二房间,有一门互通,也可锁住不通,我起床试图开啓这扇门,发现门锁居然是可以开啓的。
开门进去,房内灯光是大亮的,大床上,老公安博正和班奈狄老婆乔安娜,抱在一起,认真地在做爱做的事,二人都脸上表情紧张,气喘吁吁,正要进入紧要关头,班奈狄双手扶住挺着的大屌,在一傍站着,惊讶的看着我的出现。
这到底是一个什幺状况呀!卡露琳有些混淆了。
安博讪讪地站了起来,留下乔安娜诧异地躺在床上。
安博光着屁股,上前来将卡露琳和班奈狄推向隔壁房间,而且将门锁了,回去继续完成未竟的工作。
这可是明明白白的告诉卡露琳,他今夜要将二人的老婆互换。
班奈狄上前来褪下了卡露琳的内衣裤,拥着她上了床,她顺手在梳妆台上,抓了一个髮匝,将头髮扎了起来,今夜要和班做个够。
她今年虽然今年已经四十岁了,但她久历世事,一直情人不断,从不缺男性荷尔蒙的滋润,所谓三十如狼,四十似虎,床上功夫不输少妇,装嫩扮幼的功夫,将班奈狄迷得死脱,一会儿娇喘喊累,推人拒肏,再一下又抬眉吸舌,扭臀索爱,她骑在班的身上,拼命上下快速用她的花心一直去顶班的龟头,口中不停地喘着、叫着:
「呵哎!呵唷哇!」
「对,对!哎!唷对!就这点,对,对!」
一阵狂乱,卡露琳又被班压在身下,两支脚架在班的肩上,一块块的肌肉都在她眼前剧烈地跳动着,闪耀着美男的光茫。只听到卡露琳下腹:
「叽咕!……..叽咕!………..叽叽咕咕!………..」,不停地响着。
班奈狄囗中急促喘着:
「呵喔!……..呵呵!………..啊啊!………..」,
突然,班面容严肃,紧闭嘴唇,嘟!嘟!嘟!射了她满满一腔。
有一个念头在她脑海闪过,哇,可不要再怀上一个孩子,再一想,安博都不在乎,我还在乎什幺。
这个时候,两室之间那肩扇门开了,安博和乔安娜俩人赤条条走了逛进来,安博对我们笑着说:
「继续,继续!不要停」,
卡露琳生气地坐了起来,骂说:「变态!」,
安博还是笑着说:
「妳也没比我好到那里去呀,小班,继续!不要停」,
班奈狄真的又把我又放平了,将那支再度涨起的硬屌,当着他老婆的面,又肏进了正在往外流出他阳精卡露琳的阴道。
有夫如是,我复何言。
73 两脚宠犬
从雪梨回来,公司又恢复原状,大家各忙各的,但我们夫妻关係,已不再是以前的样子,有些隔陔,横在两人之间,不再像以前那幺亲蜜。
我知道安博整天在想念乔安娜,因为家中有长辈,班氏夫妇不可能来到家中在住,附近地广人稀,我老公家中富甲一方,大家都认识我们,所以也不可能去附近酒店或麾铁和他们就宿,所有的机会和藉口,必需是要特别製造的,为了要夜间亲自抚育宝贝儿子安极罗,我根本不可能晚间出门,原来财富太多,也会影响到人活动自由,事实上安博近来不常和我亲蜜,我空虚的下腹也常常思念班。
只有编一个故事说要跟乔安娜学法语,一个星期几天到班的家中上课,我们为此还特地去,买了一些法文课本。
班俩夫妻都在我们公司工作,但薪水不高,住家是向银行分期贷款买的,家俱布置也很平常,安博常常偷塞一些钱给她,班对安博奉承拍马,谄媚得令我有些噁心。但他床上抽插的用心程度,却使我十分受用。
这一年来,我过得很充实,白天在公司中有做不完的杂事,农忙收割季节,我也下葡萄田收穫和给员工打气,晚上回家看儿子满珊学步,牙牙学语,和俩老共享天伦,定期去学习法语(我有服用避孕药喔!),也定时做塑身体操,我觉得人生好美好。
我不知安博是怎样搭上乔安娜的,他们二人两情相悦?还是班主动将老婆献给上司品用的?不得而知,不论怎样,我都是相当鄙视他的,他只是我圂养的一条止痒的两脚狗而已,所以我也不时给他打赏一些钱财,求得他努力的回报。我也採取避孕措施,但不是为了避免生下班的孩子,而是怀上了小孩,要很久不能享受性的乐趣。
今天,在办公室中,和下属讨论,下月员工联欢晚会的细节,我们正在开会中,接到安博的秘书来电话,要我过去他办公室。
什幺事下班回家不能谈,在电话里也不能谈,一定耍我去他办公室当面谈?
到了他办公室,他告诉他秘书,要不准任何人进入他办公室,也不要接电话进来。什幺事这幺严重?什幺事这幺神密?
秘书走了出去,带上了门,室内只賸下我们二人,他很严肃地对我说:「卡露琳,乔安娜怀上了我的孩子」,
「怎幺可能一定是你的种,也许是他老公的种,你不要忘了她是有老公的女人」,
安博笑笑说:「乔安娜从她十六岁就是我的女人,班奈狄是她亲哥哥,他是被我从难民身份中选出,再安排以夫妻的身份,进我们公司上班,兄妹间,不可能怀上他的种的」,
我听了暗笑,我自己不就和小弟Andra jose 上过床。不过我才懂了老公和他夫妻的複杂关係,而且他把我推向班奈狄的理由。
「二个流浪难民男女,自称是兄妹,天天睡在一床,我不太相信他们两小无猜,你还是带乔安娜去医院捡查,确认DNA才好」,
「妳想得太骯髒了,我不想跟妳抬槓,我今天找妳来,不是要谈他们的」,
我说:「那你要跟我谈什幺」?
「妳聴了请不要吵闹,请妳安静的听,我们俩离婚吧」,
「你说什幺?」,其实我早已料到有这一天了,因为夫妻感情渐行渐远,我们到班家学法语 (?) 的次数日增,而夫妻敦伦次数日益稀少,即使做爱亦缺少激情和新鲜感,夫妻关係,其实已经早就有名无实了。
「我们离婚吧,我会照当年婚前协定做的」,他冷静地说。
「那我们的孩子怎幺办?婚前协定上没提到」,我冷冷地说,
「我无所谓,可是我父母想要留住他,他是阿丘家的骨肉」,我背上冒出一阵寒意,连他父母早就知道了,我是最后一个知道这场失败婚姻的人。
「我要带走,他也是我的骨肉,你们不要我要」,我坚持地说。
「我没说不要他,我的意思是我父母要留下他,他是我家族企业的继承人」,安博不肯妥协。
「我不要他在后母的虐待下成长,没有母亲的孩子,争产一定会输给后母的孩子,甚至生命不保,我不要留下他」,我很坚持。
「好!那我们找律师来谈,我会将妳和班奈狄通姦的照片公布送上法庭们的」,安博沉着地说。
什幺?这只狗东西、睁眼绿帽乌龟,竟已安排了这种陷阱,我顿时陷入了劣势。
「我今天起不回家睡了」,安博又说。
连他父母在内,我们冷战了十几天,我也不再到公司上班,整天和安极罗住在一起,但有一天状况突然改变,老阿丘夫妇突然同意我带走儿子,因为乔安娜产检超声波证实怀有男宝宝,继承人问题解决,按照婚前契约,分到他一年薪水扣除开销的一半,作为我离婚条件,带走安极罗回美国,在返国的飞机上,真是有些”十年一觉黄梁梦”恍如隔世的感觉,也感到被阿丘家,扫地出门打回原形。
回到纽约,我长岛的房子,已给小弟Andra Jose作新房了,我和儿子安极罗住到他外祖父母家中,爸爸今年要从学校中退休了,每天可以含饴弄孙,我偶而与澳洲Coonawarra的前同事通通电话,传来一些阿丘家的花边新闻。
上厕时,发现有一些红红白白的分泌物,气味臭臭的,有些害怕,去市区找女儿玛丽安娜的生父Jack Blacksmith医生诊治,他诊断说是一种恶性的性病,经几位同科的医生複诊,必须摘除两侧卵巢,保留子宫,我考虑了好多天,毅然接受,在纽约接受了手术。
出院后一个月,接到在Coonawarra同事传来花边新闻,乔安娜因性病产下死胎,而安博也因不明病因,住进了医院,出院后英气全消,萎靡不振,阿丘家十分低调。
有一天,我接到纽约一家律师事务所来电话,自称代理阿丘家族要索取安极罗的抚养权,我说门都没有,派人来谈,我要带我儿子去义大利住,这一下他们急了,当天下午律师事务所,就派人来家中,找我来谈,而且已经向法院申请,在法律问题没解决前,禁止安极罗离开皇后区住所。
我委托理秋律师事务所,向法院提出否决之诉,并向航空公司订票,一等法院同意,立即赴义大利侨居。
没多久,阿丘家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基于美国立国精神,人民有信仰、言论、结社、居住、及免于恐怖的五大自由,非经法律程序,不得限制人民迁居。
我再打电话到Coonawarra,向友人探询阿丘家的花边消息,她告诉我,班奈狄夫妇已因重病离开公司了,而安博却因染上重病,手术后变成一个废人了。
安博染上什幺重病?手术后变成一个怎幺样的废人?莫非也是染上了性病,阉割掉了不成?难怪老阿丘要跨洋来争孙子了。
我的安极罗,竟成了亿万财产的,惟一继承人,当初我有一些扫地出门的耻辱,报仇的机会到了。
小弟从我长岛前居所打电话来,常看到有几个可疑男子,在住所附近徘徊,很可能是阿丘家聘请的私家侦探,前来侦察我和儿子的行蹤。果然在皇后区爸妈家附近,也看到小弟所描述的人形,我找了一个机会带了儿子,搬到亡夫保罗父母在长岛的别墅,住了起来,又申请了一支新手机,将旧手机留在皇后区,让GPS追蹤软体,以为我一直在皇后区。
阿丘父母提起争子诉讼,传我出庭,我躲进Jack医师安排的妇科医院,由理秋律师事务所代递请假状,不出庭。安博全家三人滞留美国半年,始终未能见我一面,连公司营运都管不上,最后只得放弃诉讼,托理秋律师约我出面,改为民事和解。
我折腾他们够久了,才答应出面商谈和解,约在理秋律师事务所当面细谈,经我几番刁难,才出了我一口摘除子宫以来,心中的一口怨气,谈成结果如下:
1, Caroline Gee 永远是Andrew Archer的生母不可能改变。
2, Andrew Archer 全名应加母姓为为Andrew G. Archer。
3, Ambrose Archer与Caroline Gee正式离婚,赔偿赡养费美金一亿元,一次付清,往后男婚女嫁,各凭自由。
4, Andrew G. Archer归男方抚养,但每年暑假,如生母有意,应回到生母处,共同生活至少一个月。
5, 男方至少要教育Andrew G. Archer 至大学毕业。
6, Caroline Gee 分得阿丘酒厂股票三百万股,往后每年按股配股配息。
7, 双方签字经公証后即刻生效。
我忍住了悲痛,送走了宝贝儿子Andrew G. Archer。
经过这次婚姻,丧失了我作为女性主要的器官,大姨妈再也不会按月报到,女性荷尔蒙不再提供皮肤的滋润,必须依靠医师按月注射及服药,延长我的青春。
俗话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人说:女人三十如狼,四十似虎,性慾狂盛,我觉得我要抓住这残余的青春岁月,享受美丽的黄昏岁月。
我在往后的一年中,一直在雅典、罗马、新德里游走,结识了不少的牛郎,只要付上一笔费用,我就可以买到我需要的任何程度的刺激,因为我缺少了一样主要的女性器官,我永远不会感到满足,我可以一夜挑逗男伴无尽次数的作爱,直到他,第二天直不起腰来走路,我以此为乐。
使得希腊、义大利、印度牛郎界,除新手外,听到我的名字就拒绝接待,可是新手往往不堪一试,味同嚼蜡。
74 柔情战场
八月中旬的雅典,四十二岁的卡露琳,睡在雅典莲花酒店的套房内,这是一家一中等等级的旅馆,她是故意找一家,中等等级的旅馆,是为了不想太招遥,引起人们的觊觎,所以来到此间,化了500欧元,召了一个年青力壮的牛郎,共渡良宵,但此人年纪虽轻,才廿一岁,可惜经验不足,耐力又不够,到现在还不到午夜一点半,已成强弩之末,不成阵脚,害得卡露琳不上不下,有些难以入眠。
付钱辞退了他,卡露琳穿了件轻便衣服,想到酒店地下钢琴酒巴,喝杯鸡尾酒,碰碰机会,会不会有什幺豔遇,到那里一看,整个酒吧座位空空,只有二位客人,和一位调酒师,客人在那里啜酒聊天
因为客人稀少,连钢琴师也是意兴阑珊,弹奏着单调的蓝色的月亮(Once a blue moon),我点了一杯血腥玛丽,坐到客人对面,我知道我这一举动像极了酒吧中的风尘女郎,勾搭客人。但管他呢。
我抬头打量二这位客人,原来是二位都是美国大兵,一白一黑,二人衣袖上缀满了年资标带,看起来都是四十来岁年纪,坐在那里看不出身高,不过光看上身,就知道他们全是十分魁梧,白人先抬头,从酒杯口睁开大眼,静静的打量我,看了我一下,开口问我:
「How much ? and where to go ?」(多少钱,去那里?)
我知道,他一定误会我是酒吧中的娼妓,但解决燃眉之急,我也顾不得了。我跟他说了一声:
「Not much,just fellow me」(没多少,跟我走就是了),
他们二人都从座位上站起,吓我一跳,黑人兵身高至少有六呎六吋以上 (约196 cm左右) 庞然大物,我靠着他走,难得一次变成小鸟依人,白人兵也至少有六尺左右 (182 cm) ,我瞄了黑人兵裆下一眼,鼓鼓地一堆,不禁有些暗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