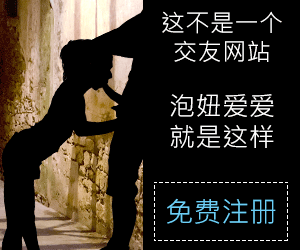卡露琳的探险(第七章) 66~70
67 声东击西
今天卡露琳到片场发觉跟往日不太一样,片场门口有些人山人海的感觉,熙熙攘攘挤了大堆人,就近询问了一下场记,发生了些什幺事,场记笑说:
「他们在排队领票,我们今天要打破世界纪录」,
我问:「我们今天要打破什幺世界纪录?」
「上次有一个中国女人在AV片上,一天内和四佰多个男人做爱,我们今天拍一部AV片,”洋女千人斩”,一个洋妞和一仟个男人做爱,打破她的世界纪录」,
我惊问:「那个女主角是谁?」
「女主角是妳呀」,
「说着玩的啦,这里一共也只有一百来个男人」,有人在说。
「不必真的是一千人,只要换换装,有一千人次,就可以了」,又有人在说。
「每二小时,休息十分钟喝水,每六小时,休息卅分钟吃饭」,
哎呀,这就可吓死我了,平常我一天内最多不过和三、四个男人做爱,这次要和一千个男人做爱,可要肏死我了,怪不得昨夜福井要给我送迷幻药和润滑油来,这分明要利用最后一部AV片弄死我,好狠的长川和福井,我要逃走,我要逃离日本,我该怎幺办。
这真叫“求天天不理,叩地地不应”。
谁能救我?
谁能救我?
谁能救我?
*** *** *** *** ***
救星来了,青藤开了他的丰田车也到了片场门口,他停妥了车,扶着腰,一跛一跛地下了车,走到我面前,小声地对我说:
「安娜,快逃吧,没有时间了,快上车,我带你走,快!」。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上了车,青藤开车快快地离开了片场,往和歌山市区走,往北经过了大阪市区不停,往北到了新大阪市区车站,青藤停了车,在驾驶座的储物箱中折下一个电器,又拿出他自己的的手机,置于一个大信封中,叫了一部计程车,预付了车资,要他送到京都大和皇家酒店217室,小林行者二郎先生收。
青藤快快地上了车,直奔高速公路,往神户方向朝南驶去。
途中,他告诉我,为了劝阻长川先生不要拍”洋女千人斩”,竟得罪了长川,被他责打了背部卅皮鞭,所以决定要救我逃出日本,现在要开车到九州,福冈机场走出日本,因为公司在车上偷装上GPS装置,所以刚才叫计程车,将GPS及私人手机,送到北边的京都去,让长川的侦测设备,以为我们在往北逃,我问他,那位住在京都,我问:
「大和皇家酒店217室,小林行者二郎是什幺人?」,青藤说更本没这个人,这是让计程车驾驶有个目标不起疑而已。
车行了三个小时左右,接近了广岛,青藤说:
「其实我们不必到九州,妳只要在广岛机场,就可以离开日本了」
「那你怎幺办,你留在日本,怎样才能躲过长川的魔掌?」,
「我是美军逃兵,我会到领事馆去自首,长川会拿我没办法的」,
「那你有没有带美国护照,如果有带,我可以帮你买机票,我们一起走」,
「我是美军,没有护照,但我有GI ID 一样可以入境美国,不过入境时可能会被捕」,
「好吧!那还等什幺,一起走吧」。
我们一起购了全日空的机票,先飞到韩国仁川机场,转机纽约,在机上,他告诉我他的身世,二次大战后,日本败战,社会上男女比例失衡,男性战死甚多,妇女必须负担主要家计,50年代大批僻乡年青女性逃进入都市,家居强罗山上小镇的,他祖母正值青春年华,到了东京,为了生活,下海做了伴酒女郎,在60年代产下了一个黑皮肤女婴,这就是他的母亲,85年她随着美国政府准许驻日美军,在日本私生子女,移居美国,她移居加州,又与菲裔美国公民非婚生下了青藤,他幼时备受岐视,生活落魄拮据,高中毕业后,投效美国海军陆战队,三年前派驻日大使馆警卫,因接到命令调往中东地区服役,不想上战场,又受长川集团利诱,逃离军旅,投靠黑龙会社。
去年青藤的妈妈,来日本探望她儿子,青藤以为她已经回美国去了,昨天他才发现,她仍在日本,在长川公司所属的卡拉OK当黑肤酒女,青藤恳求长川放过她,谁知长川竟说,她还欠公司一千万日元赌资,要替公司赚够了,才能放人,青藤和他大吵一场,今天又利用卡露琳的事件,鞭打了青藤一顿。
但到了仁川,他在机场就被美军会同韩国宪兵逮捕了,连留个连络电话都不成。
我则在仁川买了UA的机票直飞纽约。
*** *** *** *** ***
归去来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却无童僕欢迎,又缺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我那台红色的Mini小车,满是灰尘,静静地停在车库中,试了一下,电瓶居然还能发动,把它开到室外发动充电,打电话给保养厂,把它拖去加油、保养、验车。
离家四个月,我却历经二次生死劫难,终于又回到了长岛的家,不胜唏嘘。
打了一个电话,给皇后区的父母,告诉他们我回来了,但又要回到新泽西医院,去住一、二个月,再度戒毒,二星期后请他们,再来医院看我。
我二次入院,我上次诊治的医师护士原班人马都仍在,医师Dr. Jhon Hemilton 笑笑对我说:
「Welcome home,Caroline我上次跟妳说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一个月左右,会再度染毒,早晚被送返医院治疗,妳出院快半年,现在才回来,早在我意料之中,还得跟上次一样的流程再走一遍。我又被关入上次同一间牢狱似的隔离病房,每天受毒瘾上来时的折磨,及打戒毒针的戒瘾治疗,敲墙打壁的痛苦,必须在苦海中独自挺过来。
Dr. Hemilton帮我抽了血,又验了尿,确定了我成瘾毒物的成份,订定了戒除的用药日程,预定住院的时间,预定今年圣诞节前可以出院返家。
这次独居戒毒的时间较长,我在隔离病房关了一个多月,才帮我移到普通病房。
出了隔离病房,就可以打国际长途电话,因为有十二小时的时差,当天晚上就打国际长途电话,到上海市给保罗、杰布里奥尼,电话传来他厚重的义式英文:
「Hello, This is Paul Japlioni」,
「Hello Paul,It’s Caroline Clayderman」,
「呀!妳在那里呀?我从义大利回来,妳就失蹤了」,
「我上月在日本,被日本黑道下药,我现在逃到纽约,正在住院戒毒,一言难尽,下次见面时再讲给你听」,
「妳好吗?要不要我来照顾妳?」,
「我现在很好,我爸、妈、弟弟都在照顾我」,
「那我就放心了,要常跟我连络」,
「公司运作情况如何?」,
「最近公司财务稳定,正在对义大利红酒做大力的推广活动,也在米兰开了据点,销售中国产品,市场反应很有远景,我凖备要化一年的Promotion,我也找到多位,上海中国人投资合作伙伴,希望下次妳到上海,会有好消息给妳」。
「我知道你会努力的,我相信你」,
「给我妳信箱地址,我会每个月寄财报给妳的,等妳可以出院后,来到上海,我会向妳报告我的营运计划」,
「我在医院,暂时没有电脑和网路,我出院后再跟你连络,有事可以用行动电话通连,1-212-555-1xx8,时间到了我要吃药了,再见吧」,
*** *** *** *** ***
住在普通病房的好处是,不必挂点滴,也不会像家犬一样,被点滴瓶,栓在病床上,只要不在打针吃药的时间,都可以在园子里晒晒太阳或月亮,吹吹海风或淋淋小雨,看海上来来往往的船舶,或海岸上冲浪的人们,忘却一切往事和伤痛,及前前后后的男人,摆脱了毒物,感觉到又是一个全新的我,準备脱茧而出。
今夜月明如镜,清凉似水,我坐在医院园子的一角,长条的木质靠背椅上,独自一人发獃,在想念远在义大利的幼小儿女,他们都七岁了,该二年级了吧,玛丽安娜应该穿上漂亮的澎澎裙,在学校里娇笑倩兮,东跑西奔,一定可爱的不得了,小保罗应该是一个神气的小小绅士,也一定很会照顾妹妹吧。
「这位子有人吗?」有个低沉的磁性男声,说的是西西里腔义国口音的英语,打醒了我的思绪,抬头一看,他穿着病患制服,应该也是一位住院的病友,170 cm左右,不太高的身材,青年白人,背着月光,看不清他的面貌,但运动员般的身材,对女性很有震摄力。
离我没多远,明明另外有一张空着的同款长椅,他不去坐,却到我这里来要分椅子坐,分明是故意搭讪来了。
我对他脸部仔细打量,似曾相识,这个男人卅来岁,落腮鬍子,大大的眼睛,高耸的鼻樑,月下看不出眼瞳的颜色,从不认识,但却像那里见过。
突然,灵光一闪,我叫出:
「Frederic!」
「Lady,妳认识我?在那里见过吗?」
「你是 Zio Frederic 对吗?」,
「妳认识我爸? Zio Frederic ?」,
「Non ! So Jones Frederic」 (不!我认识琼斯、凡德烈克)我用义大利语回他。
「喔,我是他堂哥亚历山大,琼斯现在,他在大西洋城」,
大西洋城就在医院南面,开车走小道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那里是新泽西州的赌城,
「你有琼斯的手机号码吗?」,
「当然有呀,在我手机里,明天白天我给妳」,
他在椅子上,把身体往我的方向挪了挪,大腿靠上了我的大腿,一股男性的体味,冲进了我鼻孔,十多年来年,第一次有男人的身体贴靠上了我,久旷的我,我竟然亳无生理上的反应,大概最近一直在服用戒瘾的药物的关係吧。
「哎,我服药的时间到了,我要进去了,明天见,晚安,亚历」,
我起身往医院里走,留下他坐在长椅上,因为是晚上,不知道他有什幺表情。
68 赌场大亨
亚历山大第二天就将琼斯的手机号码给了我,我整理了一下心情,拨了一个电话给他:
「我是总管,妳是那位?」,电话里传来他的声音,
「嗨,琼斯!我是卡露琳克来德门」,
「谁?卡露琳克来德门?」,
「米兰来的卡露琳克来德门」,
「喔,卡露琳老师,妳回美国了,亚历山大告诉我,我一下还一下想不起来呢,妳跟亚历山大在一起吗?见个面吧,老师」,
「我在等医师的出院许可,出院时你可以来接我吗?」,
「应该可以,出院前一天打电话给我,我来接妳」,
「亚历山大是你什幺人?你现在是在做什幺?」,
「他是我堂哥cousin,我叔叔的儿子,他是我上司,他被法院判定勒戒,我帮我叔叔做事,所以我暂代他的工作」,他解释得很仔细,我想他一定认为我懂了,他的英文实在不灵,其实我听了,还是一头雾水。
不过我想,他叔叔很可能是,美国东区义大利西西里帮的教父级的人物,地盘在大西洋赌城,琼斯很可能是他叔叔手下的打手。
我先后碰到黑帮人物太多次了,胆子已经变小了,还是不要招惹他们吧,说完了电话,我就挂了。
亚历山大还是不时来招惹我,我只是不冷不热地对他,他有时毛手毛脚,或言语挑逗,我也是心如止水,不大搭理,次数多了,他大概也感到无趣,不太来干扰我了。
医师已签了我的出院许可,还给我做了一个身体的评估,身高173cm体重138 Lb. 比入院时胖了6Lb.,MC有一些不凖,开了一个月的保养药,医生说,我以前所服的毒物,主要成份是古苛碱和K他命类的迷幻药,但也渗了一些不明成份的动物性雌激素,扰乱了我原本的贺尔蒙分泌,所以也开了一些女性贺尔蒙,调节我的内分泌,还需要追蹤。
我趁亚历山大去打针的时间,就开了我的小红车出院回长岛走了。
车才走出了荷兰隧道,进入曼哈顿顿区,手机就响了:
「老师,我是琼斯,妳不是说出院时要我来接的吗?」
「是,我临时家中有事,所以来不及告诉你,等我处理好了,我再打电话给你,我要进隧道了,喂!喂!」,我关掉了手机。
我急于开车回长岛家中去,车子才过了曼哈顿,上了布鲁克林大桥,有些塞车,才开手机,铃声又响了,一看又是他,接起来:
「老师,我是琼斯,妳上了布鲁克林大桥呀,妳要去皇后区吗?」
他怎幺追蹤到我的?我看看四周不像有车在盯我呀,
「琼斯,你怎幺知道我现在在桥上?」
「不告诉妳,老师,这是我们业务专长,等妳事情处理好了,我会叫我公司的人,接妳到大西洋城来叙叙,再见了,老师!」。
看来他不是能即时追蹤我的车子,就是能追蹤我的手机,反正我是躲不开他的手掌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