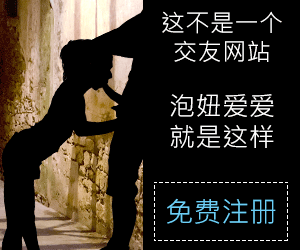背尸人
癞子懒洋洋地斜躺在门前的青石板上,一边望着坡下的吴家祠堂,一边晒着
太阳。他感到挺惬意,因爲保长来告诉他,明天一早去法场背尸,这样一来,他
至少好几天可以不必去捡剩菜剩饭吃了。
癞子本来不癞,出身于一个小康之家吃喝不愁,十五岁就娶了个漂亮媳妇,
要不是打仗的时候一颗炮弹掉在他家院子里,他本可以是镇上过得最舒坦的小财
主,可惜,那一炮炸塌了他家的老宅子,炸死了他的父母和妻子,只剩下他一个
人,从此生活就再不一样了。
他从小识字读书,父亲想让他长大了一鸣惊人,所以不会种地,不会作工,
什麽营生都不会,没有人雇他,他只能靠捡人家倒掉的剩菜剩饭勉强糊口。
起初,镇上的人看到他还都咂着舌头感歎几声,渐渐地也没有人再答理他,
孩子们见了他也毫不尊敬,只叫他作癞子,再后来,大人们也开始叫他癞子,叫
得多了,连他自己都忘了自己本来姓甚名谁,也不再愿意同人说话,甚至讨饭的
时候都只是把碗伸出去而已,懒得动一动嘴了。
这背尸的活儿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干起来的,原来,镇西五里的山洼子里是民
国开始使用的法场,每年都会有死刑犯在那里被枪毙。这里杀了人是不让家里人
收尸的,就近雇上几个人把尸体擡到附近的小山顶上扔进后面的深沟中,那时候
癞子没饭吃,又没有人雇他作工,凑巧有一次处决犯人,保长就让他去了。
那次他是和别人一起擡了一个血淋淋的尸体上山,一具尸体给两毛钱,一毛
钱就可以买好几升包谷呢。本来这种活儿别人就不愿意干,是保长硬给拉来的,
但癞子觉着这个活儿挺合适,回来就求保长让他把差事给包下来,山里人力气还
是有的,那小山也不算太高,他一个人背一具尸首上去也难不到哪里,倒可以独
得两毛钱,何乐而不爲呢。从此,他就成了这里的专业背尸人。
自打家遭不幸后,他二十多年都没有笑过,只是半年前,他住的茅草棚坡下
书。朗朗的书声打破了他生活的寂寞,使他的心情渐渐开朗了许多。
那个小学教员是个二十二、三岁的姑娘,每天都打整得利利落落的,最开始
因爲太远看不清,有一次他出门回来从祠堂前过,正好那姑娘送孩子放学出来打
了个照面,天呐,那姑娘和自己死去的妻子简直就象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站在
那里好久没动地方。
倒是那个姑娘挺大方,主动同他打招呼:「大叔,您有什麽事要找我吗?」
「啊,啊,没有,没有。孩子们读书读得好听,我在这儿听听。」
「那明天就进来听吧。」
「啊不,谢谢,我还得出去讨生活呢。」
「噢,那有时间来坐坐。」
「好,好。」
回来以后,癞子激动得直流眼泪,倒不是因爲她象自己过去的妻子,而是因
爲自打家人死后,还从未有人对他这麽客气过。从此,躺在青石板上看那姑娘领
孩子们出操就成了他生活的一大乐趣。
有她在,日子就象抹了蜜一样,就算一天不吃饭都不会觉得饿。最近,那小
学校有半个月不开课了,那个女教员也不见了,她去哪儿了?还回来吗?他告诉
自己,快了,就快回来了。
早晨,天刚蒙蒙亮,癞子就爬起来赶往法场,他有一块专门的腰牌,可以进
出法场。一到法杨的山口,就看见路边停着两辆顶棚上带灯,窗户上有铁条的汽
车和一辆挎斗摩托车,两个警察人站在那里。他心里头乐了,因爲今天这里看不
见全副武装的士兵,那就是说,今天是保密局秘密处决犯人。
癞子没有亲眼见过杀人,但听管刑场的警察说过,平时杀一个犯人要让他反
绑着跪在地上,有好多当兵的拿着长枪站在十几步外用排子枪打,犯人浑身上下
打得筛子一样,血肉模糊,背的时候都下不去手。
而保密局杀人都是将犯人反绑了,按趴在地上,如果是男犯,就由两个枪手
一边一个用膝盖跪在他们的后腰上使他动弹不得,其中一个枪手用一只手抓着他
的头发让他稍擡起头,另一手拿着短枪顶着犯人的脖子后面打,保证一枪就能解
决问题,而且也出不了什麽血,如果是女犯,那麽只要执行的枪手自己压住她的
后腰就可以了。
别以爲拿枪杀人挺容易,要不是保密局那帮人受了多少年的训练,杀人不眨
眼,一般人象杀鸡一样顶着人脑袋开枪是根本不可能的。保密局杀的人出血少,
癞子背完尸回去就不用费太大的事儿洗自己那件破垫肩和背架。
癞子不知道,这些人爲什麽被枪毙,也不知道保密局爲什麽专练杀人,只知
道这里有人杀他就可以挣到钱,就可以不必去拣剩饭,更不必去乞讨看别人的脸
色。
他知道规矩,行刑的人不出来他是不能进去的,所以得耐心的等。平时他到
这儿最多两袋烟的功夫就能听见枪响,今天杀人比往常花得时间长,一直等到日
上三竿了,才听见第一声枪响。他默默地数着:「一枪、两枪、三枪、四枪。」
因爲他知道,差不多每一声枪响就会有具尸体,而对他癞子来说,就意味着
两毛钱到手了。
半盏茶的时间,十几个戴礼帽的人从山坳子里面走出来上了车,才要走,前
面车上一个领头的探出头来对一个警察说了点儿什麽,然后癞子便被叫了过去。
「你是背尸的?」
「是。」
「里面有四个。你想干什麽都行,」他向山坳子的方向呶呶嘴,伸手掏出几
张小额钞票递过来,癞子伸手去接,那人的手突然又抽了回去,表情突然变得很
怕人:「不过,不许对任何人说这里的情况,不然的话,我就让别人到这儿来背
你,听懂了吗?」
「不说,不说。」癞子急忙小鸡啄米般地点着头。癞子没有什麽朋友,即使
不嘱咐,他也根本不可能对别人说什麽。
车走了,那两个警察也骑上摩托走了,拿到钱的癞子拎起背架,另一手把披
肩往肩头一拾,一路唱着走进了山坳。
到了每次杀人的地方,只见地上铺了四张大竹席,四具尸体一字排开,头朝
山坡趴在地上,双手水平交叠反绑在背后,全身都光着,露着一身白花花的肉,
虽然看不见脸,但仅从那光滑的皮肤和玲珑的身体曲线就能看出四个都是女人,
而且都是非常年轻的女人。
癞子背尸这麽多年了,秘密处决犯人时,行刑前刽子手们把犯人身上好一点
儿的衣服扒去卖钱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过那些犯人大多是男人,女的本来少见,
而且,刽子手们也只要值钱的西装、旗袍、皮鞋、手饰、手表之类,象这样子连
内衣都剥了拿走还是头一次。
那光光的女人身体让癞子的心「怦怦」地狂跳起来,下面不知不觉中已经胀
得生疼。癞子知道刚才那人话中的含意,自己一个早年丧妻的老光棍,趁背尸的
机会在女犯的尸体上动些手脚也是人之常情,反正她们都死了,不会喊他强奸,
而且尸体一丢进山沟,便一切痕迹全都消失了,不用说这是秘密行刑,就算是平
时正常的执行,尸体也是他这个背尸人独自处理,没有人去管他。
癞子不是正人君子,而且,象他这样穷得连家都没有的人,还有什麽体面可
言,他也同别的男人一样需要女人,但没有一个人把他当人看,更不会把女儿嫁
给他了,所以,那个刽子手头头猜得不错,每次处决的犯人中有女性的时候,癞
子都决不会放过她们。
山上丢尸的崖边有一块平平的大石头,那就是每次癞子享用女尸的地方,他
会在那里把女犯的尸体剥光了,发泄一通之后,拎着两只脚直接扔下去,而她们
的衣服,他就带回去,或卖或撕了当补丁。
癞子玩儿女尸是不会挑挑捡捡的,无论是四五十岁的半老徐娘,还是十来岁
的小女孩儿都行,实际上他也没有挑挑捡捡的资本,除了尸体,他还能找谁发泄
呢?
今天,这四个可不一般,从背后看去,腰儿细细的,臀儿圆圆的,除了脖子
后面那一个不大的枪眼还往外冒着鲜血,整个肉身粉捏的一般白白嫩嫩,一看就
知道最多不会超过二十五、六岁,而且都是城里人。看那齐耳的短发,是女学生
吗?不知长得怎麽样?
人就是这样,有吃食的时候撑死了都吃不完,没吃的时候牙缝都塞不满。平
常日子里,一年一年都赶不上一个女犯,难以解渴,今天一下子就是四个,根本
吃不下,如果不是因爲尸体放不住,癞子真想把她们都搬回自己的茅草棚里面慢
慢享用。唉,没法子,自己天大的本事,也总得放弃两个,不过,不知道哪一个
最好看。
癞子站到四具女尸的脚后,一个个仔细看着,想先从背影找出一个最好的。
最外边一个个头不高,但身儿细溜溜的,屁股窄窄的紧紧夹着,一看就是十
几岁的小姑娘,他还记得,自己那个十四岁时嫁过来的小媳妇的身子就是这般样
子;
第二个,身体虽然长开了,臀儿宽宽的,但腿子细细的,中间留着宽宽的缝
子,应该也是个刚刚发育完,肉还没有填实的稚嫩少女,这种样子多半是个十七
八岁的姑娘;
第三个和第四个都已经长成了,宽宽的臀部和丰腴的大腿显示着成熟女性特
有的媚力。看来看去,这四个各有千秋,难分上下,要说身条儿好,还得是那后
两个岁数大一些的,但两个小的那一身肉嫩得能掐出水来,也割舍不下。
他又转而去关注她们的年龄和姓名,因爲好的名字也能使女人的美丽增色。
一般的犯人行刑时,背后有亡命招牌,秘密处决的只在脚腕上拴一个小纸牌
子,那是用来验明正身的。他读过书,虽然离举人进士差得远字到还识得几个。
他先拉起最外边那个女孩儿小小的脚,那脚丫滑滑的,软软的,让他爱不释
手,拉过上面的小牌子,写的是「吴小婵,十五岁,学生……」,他伸手捏了捏
那圆圆的小屁股蛋儿,软软的,滑滑的,捏起来非常舒服,随着那屁股蛋儿被捏
得变形,他看见一个黑黑的小屁眼儿。「不错,真不错,不知那个怎麽样?」
他又来到第二个女尸后边,同样的两只嫩脚丫,同样的嫩肉,她叫赵青莲,
十八岁了,也是学生,这一个不用捏屁股,由于腿太细并不拢,她的屁眼儿就露
着,也是小小的,黑黑的。「好!也好!」
第三具和第四具女尸都相对丰满些,两腿并得很紧,一点儿缝隙都没有,不
过仍然不失于苗条,属于那种漂亮女人的真正美体,那两双脚也软嫩得很,而且
十分纤细,屁股比两个小姑娘更圆,更有光泽,捏上去弹性十足,这两个一个叫
筱红英,二十四岁,职员,一个叫那丽,二十二了,小学教员。「嗯,这四个都
不错,可让我挑哪个呢?看看下身儿吧。」
癞子站起身来,用脚把四个女尸并拢的腿都分开,让她们的私处露出来。
只见两腿分处,四个女人的私密之处全都暴露出来。吴小婵的阴唇薄薄的,
白白的,生着一点儿又细又软的茸毛;赵青莲的阴毛很浓密,把整个腿裆都给占
满了,虽然掩住了阴唇,但黑黑的反而更加吸引人的目光;
筱红英的阴唇比较厚实,呈暗褐色,象男人的卵子般带一点儿皱纹;而那丽
的阴唇不薄不厚,顔色也是白白的,羞处的毛不浓不淡地分布在阴唇前半部分。
除了筱红英的两片阴唇稍稍裂开,露着里面的小阴唇和那个深深的洞口外,其他
三个女人的阴唇,无论厚薄都那样夹得紧紧的,一看而知被抓来之前还都是大姑
娘。
「狗日的!我说杀个人怎麽花这麽长时间!」癞子嫉妒地低声骂起来。他不
是在骂四具女尸,因爲他喜欢,还喜欢不过来呢。他骂的是保密局那帮刽子手,
因爲不管少女也罢,少妇也罢,四个女尸的私处都是湿湿的,沾着大量粘粘的液
体,癞子是过来人,当然知道那是什麽东西,再看那三个大姑娘的肉缝后边,还
都带着一丝鲜血。
「老子不过弄弄死人耍耍,这群狗日的,活生生就把四个女伢子给日了。看
流了这麽多东西,也不知道几个男人弄一个女伢子。唉,要是老子会杀人多好,
也整个活的耍耍,也不用这麽辛苦地背死尸了。」
他实在是嫉妒得不得了,蹲下去仔细查看四个女人的私处:「这一个血往屁
眼儿流,一定是躺着被日的;这一个横着流到大腿上,应该是侧躺着让人家给坏
了;这个也是躺着干的;嗯,这个那丽怎麽前后都有血,看来是先躺着日,换了
人又趴着日的。」一边判断,一边心里想着当时的样子,癞子觉着浑身的血都涌
到脑袋上去了。
「该老子了。」他有些顶不住了,赶快把那个最小的吴小婵翻过来,细长的
脖子前面被炸开了一个大洞,使她的脖子几乎断了半边,小巧的圆脸白白净净,
微显露出两道泪痕,一直流到耳朵后边。
「一定是被男人日的时候哭的,挨,别想了,睡吧。」他对她说,然后给她
把眼皮合上。再看她的身子,两颗奶子白白的,小小的奶头尖尖的,粉红色,非
常诱人,不过,奶子小得象山芋蛋子,抓不住,「算了,换一个看看吧。」
那又翻过赵青莲,瓜子脸,直直的鼻子,小小的嘴,眼睛长长的,弯弯的,
挺立在胸前,扁平的小肚子上有一个圆圆的。深深的肚脐,高高的阴阜上一丛黑
毛一直延伸到长长的两腿中间。
「嗯,这一个不错,先来她吧。」癞子把她的两腿尽可能分开,然后跪到她
的两腿中间。他的身体早就準备好了,三两把扯下身上的破布片,露出一个髒兮
兮的光身子,挺起已经胀得生痛,黑乎乎,象小杠子一样的阳具,然后一手分开
姑娘的阴唇,一手扶住阳具插了进去。
「嗯,还是温温的。」他很兴奋,先慢慢磨了磨枪,感觉里面滑溜溜的挺顺
当,便奋起雄威,长趋直入了。不知弄了多久,他感到那姑娘紧紧的洞穴已经夹
得他快要放了。
「不行,不能就这麽完事,还有两个更好的呢。」想到这儿,他停下来强忍
住沖动把自己抽了出来,跪在那里忍了半天,直到那股难以驾驭的劲头儿过去。
转身翻过筱红英,她长着一张胖乎乎的圆脸,是那种最典型、最传统的美人
形的腹股沟交彙的三角地带,无论什麽样的男人都不能不说一个好字。「这一个
更好。」
癞子立刻扑上去,一下子就趴在她身上,急不可待地抽插起来。这一个的洞
穴不如赵青莲紧,这也正常,她不是处女,也许还有过孩子,但那肉乎乎的身子
却给了癞子更好的感觉。癞子发疯般地折腾了许久,直到自己快射了,这才又停
下来,他还想要那第四个。
翻过那身子,果然,她的两乳又圆又挺,又白又嫩,顶着两颗粉色的葡萄珠
儿,身子的曲线非常顺畅,阴毛也不疏不密恰到好处。
「这个最好!」癞子撩起她长长的头发,露出被遮住的脸庞,然后他就愣住
了。那是一张多麽漂亮的脸,长圆的脸蛋儿,尖尖的下巴,圆圆的耳朵,弯弯的
一双秀目还含着泪水,仿佛向人倾诉她的不幸遭遇。
然而,那又是一张多麽熟悉的脸啊!早在二十年前,他就在自己的婚床上见
过,他曾经亲着这张冰冷的小脸,伏在她赤裸的身上,把男人的一切力量都放在
她两腿间,二十年后他又见到她,笑得是那麽温柔,那麽迷人,重新给了他生活
的乐趣。
是的,她就是那个小学教员,那个与癞子的媳妇长得一模一样的年轻姑娘,
那个曾经叫癞子作大叔的姑娘。
象一盆凉水浇在身上,癞子一腔的欲火灭了。他怔怔地跪在那里,不知出了
什麽事。她是个多好的姑娘啊,从她来了,就从未与人争吵过,大人们喜欢她,
孩子们喜欢她,癞子更喜欢她,她究竟得罪了谁?!爲什麽要杀了她?!爲什麽
临死还让她饱受羞辱的煎熬?!这都是爲什麽呀?!
从那天回来,就没有人再见过癞子,直到几个月后,保长去茅草棚通知他背
尸的时候,才看到癞子已经躺在乱草堆中成了一具白骨,手里还捏着那天挣来的
八毛钱。他的身上伏躺着另一具骨骸,不知是男是女,颈骨有两节已经成了小碎
块。
死了人,保长得去报官,警察局来堪查的人说,那具骨骸是个女人,是被子
弹打断了脖子死的,应该是被保密局处决的政治犯,但保密局比警察局地位高,
他们的事情属于军事秘密,警察局无权过问,此事就这样罢了。
从此,这里再没了背尸人,保长又得挨家挨户地找人去擡死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