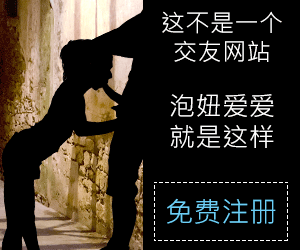毒蜘蛛
很高兴台湾网友「欣华」又有新作品了,可惜的是她或会封笔一段时间了!在这里再次感谢她!这次的故事背景会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喔,事不宜迟,请收看…….
如果有朋友想转载这篇作品,请保留此段或注明转载自,谢谢!- 搜性者 2016.12.01
作者:简欣华
(一)新婚夜一场噩梦
1940年11月6日夜,日寇侵华战争仍在进行之中,在安徽太平旧居,红烛高烧,锦幄初温,吵闹而忙碌的一天,终于过去了,宾客也散去了,我和新郎宏辉哥的结婚大日子,终于到了最重要的尾声了,我俩在新房内的小桌上,共饮合巹酒,我们等待这宝贵的这一天,已经四年了。
宏辉是我安徽大学同系高一届学长,在我入学那一年迎新会上结识,可以说一见倾心,一同坠入情网,我四年的求学生涯,可以说也是我的一部恋爱史,我俩花前月下,互诉情愫,也许下了终身结缡的诺言,共渡我们人生旅程,準备在我毕业后,儘快完成婚礼,开始共同经营人生,开创美好的将来。
徽式老宅,房院很大也很陈旧,是宏辉哥数代袓居大屋,因为最近县里才有民用发电厂营运,虽然有电灯照明,但供电还不太稳定,喜宴刚完,宾客才散去,马上又碰上停电,所以点上了蜡烛,因新郎新娘已进入洞房,临时请来帮忙的人们,也收拾打扫完宴会的残席,分别散去了,因为今年天冷的有些早,洞房中还生了一只大火盆,新房内已安静之极,只能听到二人的呼吸声,及烛蕊曝裂劈啪声。
我不善喝酒,才喝了二、三杯甜酒,酒意就冲上了脑门,知道即将发生闺房中的事,心中一面非常期待,一面又十分忐忑不安,宏辉放下了筷子,站起身来把手伸向我,低声说:
『采苹,不早了,我们上床吧!』,
我害羞地点点头,站起身来和他携手走到床边,满脸涨红,我掏出一片小方巾先铺在床上,準备承接我的处女落红,再把枕头和被褥整铺好了,褪去外衣,把二人脱下的衣服,摺叠好了,整齐地放在床边的椅子上,先钻入了被衾中,我解开了扪胸束绑,等待我的新郎来靠近我。
早先,我从校中同寝室已婚的女同学那里,早已被告知道,也从小说书刊中知道了,女孩子第一次这件事,都告诉我会痛。但有人说不过痛二、三分钟,也有人说会痛好几天,有人说只像铅笔刀刺到,不过尔尔,也有同学说像被军刀扎到,痛入骨髓,莫衷一是,害得人家好几天前就心情忐忑,坐立难安,现在已是最紧张的一刻,双手感到有些微微颤抖,躺在衾中等待他进被中来。
宏辉哥也脱了外衣,钻进了被窝,靠外床跟我并肩睡下,把我轻搂在他怀中,我耳朵紧贴在哥温暖的胸膛,听到他心脏有力地在呯呯跳动,我非常紧张,知道自己心脏也在加速跳动不止,我已预知哥的下一步动作是什幺,恋爱了四年,花前月下,我俩牵手、亲吻、拥抱,抚摸、都做过了,唯独最后一关,一直要保守等到今日,才要来完成,即使二人都有要儘早完成这个仪式的渴望。
『采苹,今天妳辛苦了』,他说。
『哥,我觉得今天自己像一个牵线木偶,被指挥着东跪西拜了一整天,累到是不累,有些好笑而已』,我说。
他用手在我背上轻轻抚摸,他的手有些冰冷,从脊骨一直下行到臀部,喔!我全身起了鸡皮疙瘩,冰到不行,也痒到不行,有些手足无措,往他怀里直钻。
宏辉将自己内衣也脱了,精赤条条地也抱住了我,睡在我外床的左侧,他伸出冰冷的手,摸向我的胸脯,我打了一个哆嗦,他将脸靠过来索吻,我回应了他的吻,但我双手不知要怎样摆放,他抓住我的右手放在他坚硬勃起的生殖器上,平生第一次,摸到他的大生殖器,我不禁脸上红潮上昇,紧闭双眼,想抽回我右手,但他坚持不放,我只得照做。
他伸手进入我丝质内裤,内裤是新的,腰间橡筋束带很紧,有些碍到他手的活动,他用脚将它叉了下去,伸手轻轻揉磨我的阴蒂。
哎呀!不得了,它又痠又麻,我缩做一团,想抽手回来,把他的手压住,不许他乱碰,但又捨不得放开他的生殖器,我感到下面一直在冒水。
我分开了双腿,闭上双眼,迸住了呼吸,等待他爬上我身上,心中一直在计数,1,2,3,4,5,6 ……,咦!他怎幺没有下一步?
突然,宏辉哥猛一下往后一仰,”呵!”叫了一声,倒向床下,整个人摔到了床下,我睁开了眼晴,看到有一个穷兇极恶的麻脸匪徒,用一圈麻绳套在宏辉的脖子上,宏辉脸孔涨得通红,叫不出声,双手抓住绳套挣扎,想是呼吸不到空气,我放声大叫:
『啊…………,咳…………』,我也被另一个匪徒用麻绳套住,喉咙也叫不出声。dwkm.xyz我看到有五六个匪徒,不知什幺时候挤进了新房,有人拿着长鎗,有人拿着盒子炮(驳壳短鎗),有人拿着短刀,一个个兇神恶煞摸样。
宏辉被匪徒用麻绳绑住,裸身梱在椅子上,另一个匪徒,用细麻绳将我手脚,大字型分别绑在大木床的四支边柱上,嘴里塞上我的丝质三角裤,一个好像头子似的匪徒,开始逼问宏辉金钱的存放地点:
『胡少爷,我们是抗日游击第三纵队,恭禧你新婚,顺便来贵府要一些补给,希望胡少爷爱国不后人,补助我们五万元大洋,将来打退日本鬼子,政府一定加倍归还』,这个好像是头子的年青人,操了一口安庆口音说。
『大爷,我们是破落户,父母早亡,根本没有钱财,不要说五万元大洋,连五万元储备券都拿不出来,你们找错人了』,宏辉颤抖地哀求说。
『胡说,你骗谁呀,你有钱读大学,有钱讨新娘,有地放佃租,还向我们装穷,说没有钱,你在骗谁呀,今天要是不拿出五万元大洋,就要你好看,不要浪费我们时间,快说,你们金库在那里?不要放考验老子们的耐心』,年青的土匪头子兇狠地说。
『大爷,我们是破落户,我读大学,全是族中公积金出的钱,讨的新娘她也是父母双亡,没有三聘六礼,连酒席钱都是欠的,要用收的贺礼钱支付,我真的没有钱』,宏辉对土匪头子说。
『你不要唬弄我们,你有田地出佃,吸佃户的血,黑心地主,跟我们哭穷,今天你不拿出钱来,老子们翻了脸,你吃不了,兜着走,好好跟你说,你唬悠老子,老子杀了你老婆,看你还说不说』,
『大爷,我只有六分贫瘠的山坡田,种不出什幺稼穑,让别人随便承种,我从来没有在缴田税,所以也不收佃租,也不信你们可以去问种我家田地的人,你就会知道』,宏辉辩说。
『大爷没有这些法国工夫,听你哭穷,不给点颜色你看看,不知老子厉害』,头子手一挥,对部下使了一个眼色。
有一个匪徒,接到指示,用手鎗把手,狠狠地在我脸上砸了下来,打在我嘴上。
『啊!…………』,我痛澈心肺,感到一阵腥味,知道至少断了一颗以上的牙齿。一低头,颈部绳索一紧,我无法呼吸,口中本来就塞了一条三角裤,口里也叫不出声音来。
『大爷!我一家一当全在此处,你们尽量搜吧,你们能找到的,什幺值钱的都归你,饶了我老婆吧,她什幺也不知道』,宏辉哭了。
『搜!』,那个年青的匪徒下令,室内外一共有十个人左右,就裏裏外外开箱砸桌,到处翻查,最后找到一本(伪中央政府的中央储备银行)储金簿,储金簿中尚有存款十万余储备券,及约合鸡蛋一斤价值的现金六万一仟三百元储备券,匪徒们大喜过望,骂道:
『说家中没钱,哭穷,这是什幺?』,
『大爷,你们来晚了,这些钱,去年来还可以买几钱金子,今年来只够吃一碗排骨麵了,你们想要,就请拿去吧』,宏辉哀怨地说。
『他妈的,你笑大爷们不认识字吗,你今天收的贺礼呢?快拿出来交给老子们,肏你妈,不然要你好看』,一个麻脸缺了半只左耳的中年的匪徒开骂了。
『大爷!今天我请的全是同村的近支亲戚,国家战乱这幺多年,年头不好,大家都是穷哈哈的,那有什幺贺礼呢,现金已被包酒席的老闆收走了,剩下的都在大爷手上了』,宏辉有些哀求了。
『大爷们也是化了一番功夫才到你们这里的,难道要我们拿这幺一些钱回去!我们抗日游击第三纵队,是不会空手走的,快拿大洋出来,不然不要怪我们心狠手辣,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这个汉奸快说!钱藏在那儿?』,另一个满脸鬍渣瞎了一目的匪徒骂了。
『大爷!我们山城老百姓,怎幺会是汉奸呢,大爷开恩哪!』
匪徒头子看看屋内所有箱柜,和可容物件的抽屉,都已破坏逮尽,找不出任何可藏钱财的迹像,也找不到任们何密室的可能之处,十分失望,翻开大床被单,绵垫也没有任何发现,大概已知道抢错对象,一无所获。
这个年青匪首,挥挥手,所有匪徒都退出了新房,只留下他和我们夫妇二人,他找了一件衣服,塞满了宏辉嘴巴,走到床边,脱掉了裤子,露出一支昂首的大屌,爬到我身上。
我惧怕极了,浑身抖擞,想大叫,口中塞满了东西,却叫不出来,匪首索性就把我口中的内裤,及一颗断裂的门牙挖出来,让我大叫,下面的狗鸡巴,狠命的从阴道肏了进来,我初经人事,又惧怕已极,浑身哆嗦紧绷,阴道极其乾燥,一点油都没有,痛得我几近昏晕,大声号叫,匪首用右手撑住体重,左手按住我嘴巴,我头一偏,在他左腕上,狠狠地一口咬住不放,他拼命要挣脱,但下面仍在狠命不停地肏我,直至五六分钟后射精,才拔了出来,我也才鬆了口,他左手手腕上七个齿痕,上三下四(我口腔内被打断了一支上门牙) 深入肉内,沁沁冒血,他用力抽了我二个耳光,才下床穿裤走出新房。
我看到宏辉已晕到在捆住他的椅子中,我则四肢被栓在床柱上,仍无法动弹,又是伤心又是疼痛。
接着那个鬍渣满面瞎了一目的中年匪徒,走了进来,也脱了衣裤,一样亳不怜惜地肏了我,我知道,我下面一直在流血,但我无能为力,只能像一条死狗似的任人宰割摆布,匪徒们一个个轮番上阵,我晕了过去,不知有多少匪徒上过我。
不知有多久,我悠悠醒来,天已快亮,我利用角柱的方角,磨断了捆绑我右手腕的绳子,才脱困。去解救宏辉哥,但发现他已经断气很久,脸色发些黑,四肢僵硬了。
(二)皇军少佐村田君
县理派人来勘查强盗杀人轮姦案后,出榜悬赏抓匪,但毫无线索,只知匪徒一帮人不到廿人,自称抗日游击队,又称十三纵队,又称十七大队,又自称十六路军,出没在长江皖南、皖北两岸,到处打杀掳掠,犯案无数,但一直抓不到,我办妥埋葬了宏辉的丧事,被轮姦案,尽人皆知,在太平没有容颜再耽下去,等到身心的创伤有些痊癒后,告别了族中长辈,一个人带了仅剩极少的一些钱,来到了杭州,在宏辉一个族叔家中住了几天,发现他不怀好意,有意无意的碰一下我的臀部,腰部,有一次还故意碰到我的胸部,使得我十分厌恶,(我的胸部,在被匪徒破处后长大了很多,在那个时代,除风尘女人外很少有人用胸罩,大多使用长巾扪胸,我把它捆得紧紧的),只得在下城区一个巷子内,赁居了一个小房间独居,我一个举目无亲的单身女人,为了生活,自己到市内一家名叫金谷很大的舞厅,应徵伴舞,结识了一个女大班赵大姐,投靠在她旗下,以大学毕业为号召,张艳帜下海,伴舞之外,也开始半公开做一些生张熟魏的生涯,赵姐租了一套二个寝间的套房,她自己住一间,空出一间,作为旗下姊妹的襄王和神女幽会的露台,她则抽一些夜渡资分成,作为房租补贴。我也找一些恩客,来此偶住。
这时杭州在日寇佔领之下,舞厅日本皇军客人很多,为了扩大顾客层面,多赚一些收入,我开始报名补习班,学习交际日语,同时也学习普通话,改掉一些皖南乡音,以掩灭一些生命中悲惨往事。
因为我自您认姿色不错,舞技也很优美,又称自己是齐鲁大学商学院毕业的头衔,很快出了一些艳名,很多客人向赵姐探听,希望能作我入幕之宾,但我慎选对象,只有少许我看得上眼的人,才能作我入幕之宾,很快我爱上男女作爱的刺激,尤其是剧烈的冲刺及事后浑身大汗的互抱和拥吻,以我现在的艳名四播的程度,我可以夜夜笙歌,天天生张熟魏,收入可观,但我仍坚持我的原则,不是我看上眼,决不会接纳。
赵姐带我去装了子宫内避孕器,也提供如意袋防止性病(那时还没有发明塑胶材料,而是用丝绸製的保险套,前端浸泡一些防水薄材加强避菌,)。
今天,舞厅来了一位身穿军服的皇军少佐,身材不高,我穿了高跟鞋还比他高一些,大概久经军事训练,一身肌肉,很是精壮,留了一撇小嘴髭,会讲一些破碎的中国话,而我会讲一些破碎的舞女日本话,二人一起跳了不少支舞,付了我不少舞票,他找来我的大班赵姐,想要带我出场,我向赵姐点头表示同意,赵姐告诉他,她有房间可出租,他就叫了车去了那里,车中他告诉我,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名叫村田敬次郎,来自日本鎌仓,我告诉他我名叫赵芬芳,乃是赵姐的姪女,来自苏北,他说他不太会发音芬芳二个支那字,帮我起一个日本名字叫我”爱子”(エゴ)好了,我们到了赵姐家,我领他进了她的房子,帮他泡了一杯杭州龙井茶,他很客气们的说:
『ありがとう-』(有难,多谢),很有绅士风度。
我踢掉了高跟鞋,坐在床沿,像小鸟依人似的坐进他怀中,他付了我二张百元日本军券,这是沦陷区裏最能派用场的东西,我也很爱他浑身一块块的肌肉,用手捏他的臂二头肌,他却伸手脱掉我的上衣,解开了我的胸罩(我下海后,不再用扪胸,已改用胸罩了,取它一个穿脱极为方便)。
他站起身来,放下了我,脱去佩鎗和军装上下衣,光身裸抱住我,低头轻咬我乳尖,我已经三天没有男人了,立刻就勾起了蓄储了三天的情慾,乳尖发硬,左脚站在地上,右脚抬起绕住他,夹在他右臀上,用阴户口去碰他的肉捧,他把我推到在床上,扑在我身上,用肉捧来找寻入口,我低头看他的武器,不是太长,阴毛也是短短的一簇,肉棒粗粗壮壮的,很配他的身材,我分开了双腿,便于他的进来。
龟头有些粗,包皮也有些厚,磨擦到阴道内壁时,如意袋又不太合身,磨擦时有些痛,但也增加了一些快感,刚开始他慢丝条理,缓缓地肏入,阴道内水不多,他调好呼吸,好像老朽一样慢吞吞地进进出出,引得我急死人了,不由抬了几下臀部催他,他笑了一笑,突然像三菱重工军用卡车似的飙车猛冲,而且愈抽愈快,他粗壮的龟头不断摩擦阴道壁,我只能紧紧地抱住他上身,拼命抬起和摇动臀部,不让他动作太大,他大概有些误解,以为我情慾高涨,更加变本加厉狂风暴雨的努力想征服我,不停地顶到我的子宫口。
我累到不行,喘息不止,大声呻吟叫床,不禁高声大叫:
『啊!…………啊!…………ビッグ野郎!…………AKUTO恶党!啊!…………啊!…………』
他听了,更加剧烈加速捅我,我只得疯狂地大叫大吼,披头散髮浑身大汗淋漓,喘息更大声,一口咬住他臂肉不肯鬆口,他一吃痛,大叫一声,感到他下面狂洩射了一大堆,颓然退出了我。
我也鬆开了口,看到他手臂上有二排鲜红的齿痕,上三下四一共七个齿印(那是我被土匪打折了一颗门牙的结果)。
我对他做了一个抱歉的表情,说了句:
『すみません』(对不起)。
他看了一下伤口,摇摇头,轻轻地说了一句:
『だじょうぶ』(大丈夫,没问题)』,一把搂住我,抓起床边的杯子喝了口茶,放下水杯,并头和我睡下。
这是我活到廿四岁以来,第一次做得最爽的爱。
我听到房门开啓和关上的声音,隔壁房里有了人的动静,知道晚上十二点多了,赵姐下班回到家里了,我用手指放在口上,嘘了一下,对少佐比了一个不要出声的姿势,谁知他毫不在乎,翻身又爬在我身上,问我:
『もぅいちどぅですか?』(再干一炮?),我点点头。
他又大起大落地插进了我,这是一个受过严格体能训练的军人,才一下就恢复了体力,肉捧更加坚硬,一上来就比适才更出力地用力捅我,我一下就感到尿道不停地冒出水来,他诧异的问我:
『Fun Shu Tus Ga?』(潮吹吗?),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幺,涨红了脸回答不出来。他低声问我:
『げんきですか』(元气吗?妳还挺得住吗?)。我点点头,低声回答说:
『だじょうぶ』(大丈夫,没问题),他夸了我一句:
『いいよ』(好棒!)。
他低头吻了我,又再出力地抽插肏我,我阴道开始收缩,紧紧地咬住他的肉棒,口中大声乱叫:
『哇[email protected]%$^$$&*() 喔#$^%&*(%啊_4 #$#$%&^*&*(&)』胡言乱语不知所云,忙乱间,看到赵姐穿了一套睡衣,在房门口探了一个头又走了。
因为刚才他已经洩过一次,这次他肏得更深更久,加上我阴道一吸一放又咬得比较紧,我疯的更狂野,更主动,我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能这样淫蕩开放。
『妳大大的好棒!』。他用中国话批评说。
不知道他肏了我多久,也不知道我潮吹了多少次,也不知道少佐是什幺时候走的,睡醒时己是上午十点多了,还没睁眼,感到又有人在玩弄我的乳尖,我以为又是少佐在吵我,伸手到他胯下,想抓住他调皮的肉棒,却在他胯下抓了一个空………好像是一张和我一样的湿漉漉的屄。
我惊惶地发现他竟是一个女人,睁眼一看,睡在我身傍的竟是一丝不挂的赵姐。
『赵姐!妳怎幺了?』,她对我嘘了一下,把我的手拉到她毛簇簇的胯下,用大腿夹得紧紧的。也伸到我胯下,用姆指与食指搓我的阴蒂,但是因为我才激烈地做了一夜的爱,体力和性敏感度都降低不少,对她的挑逗不易有什幺反应。
但她是我的大班,也是我的老闆,我生计的衣食父母,我俩就是鸨母跟妓女的关係,尤其是更忌惮她身后的流氓,想到这里,不禁一凛,马上扮出一付小心翼翼,加上非常顺从的姿态,向她献媚,但我从不知道,女女也可以做爱,就任由她摆布。
她爬在我身上,摆了一个69姿势,低头认真地嘬吸我的小阴唇,用鼻子嗅闻我的阴道口,偶尔用舌头在我阴蒂上轻舐及嘬吸,或用门牙磨磳,害我一时不知如何回应,只有依样画葫芦,也同样玩弄她的老屄(赵姐今年,据她说卅九岁,我看至少四十五岁,说不定有五十岁了),不知是不是刚上过小号,闻起来有些臭臭的味道。
她一直在玩我下面,渐渐阴道口有些分泌,她一直玩,一直弄,分泌愈来愈多,变成整个湿答答的,她从床边脱下门傍的衣服堆中,抽出一支好像是灌满生黄豆的如意袋,很像男人的大屌,乘我不备插进我下面,因为阴道内淫水充沛,啵!一下就顶到了阴道底部,直顶到了子宫口,我机伶伶抖打了一个冷颤下,口中:
『喔!…』了一下,她坐起身来,把我两脚朝天,就用它玩我,那黄豆将如意袋灌得紧紧的,在阴道内比真的男屌还硬,颗粒磨到阴道壁,呵!好爽啊,在阴送道内直出水『 :
『叽咕,叽咕』,响个不停,很爽,真他妈的很爽。
她一直把我溢出的淫水往肛门口搽,用姆指扣紧了肛门,顺着愈出愈多的淫水,姆指扣进了肛门,有些痒:
『姐!妳在做什幺?』我抗议,她笑说:
『我来帮妳开苞』,我还没来得及抗议,她食指已深深地插了来,我觉得还可忍受,就由她在里面左转右挖,尤其碰到其中某一点,比插到阴道底一样爽快,我不觉禁大声呻吟 :
『嗯!嗯!嗯!………喔! ………喔!喔! ….』
没多久,觉得肛门很疼,低头一看,她竟用那支假屌插了进来,而且上面还有些血迹,我作势要抗议,她用手压住我口说:
『别叫,忍一下,好处就要来了,快成功了,妳真的天生就是一只卖屄的好材料呀,别吵,老娘替妳好好开通一下,忍一下,等会我给搽些药,妳会常常记着我给妳的好处』。她就专心一意的大力抽插起来,刚开始很痛,慢慢习惯了,有些麻痺了,也就没那幺痛了,最后,愈来愈舒畅,哎哎大叫:
『呀!呀!……哎哎!…….喔…….姐姐…用力..别停』。
我正在忘神大叫,赵姐,突然拔出了假屌,说了声:
『好了,我手痠了,换妳替我服务吧』,在衣服堆由裏掏出一小罐药膏,帮我肛门搽了一下止住了肛门开裂流血,搽上后肛门痒痒凉凉的,舒服极了。
当夫天下午,我渴睡极了,在赵姐屋里,睡了一整天,傍晚也没去舞厅上班,下午睡够醒了,洗了一个澡,感到屁眼很痒,很想找人帮我肏一下……….,
哎呀不好!一定是她昨夜替我搽的药在作怪。
(三)血腥的日本舞俑
发现用日记式的第一人称说故事,真们的很不方便,要用到无限次的”我” 觉得很累赘,以下改用第三人称说自己的故事。
昨夜和赵姐在她房中巅鸾倒凤,睡到下午三时芬芳(我)才醒来,盥洗完了,先好好地洗了一个澡,但才洗净全身,大姨妈却又来了,将它处理好了,还是要去上班,赵姐下厨,犒赏了芬芳她一份早餐作为慰劳,下午四点,就去伴茶舞,熟客还不少,有些应接不暇,还坐了不少抬子,赚了好些舞票。
晚舞开始,就看到村田少佐穿了西装便服进了场,一会儿,他就来邀舞,在舞池中,他问爱子昨天怎没上班,告诉他大姨妈来了,行动不方便,他点点头表示暸解,他要爱子再去赵姐家中,爱子告诉他大姨妈来了,怎能做爱,村田摇摇头说没问题,在血泊里肏屄更刺激,爱子嫌他讲话太粗鲁,要他说话文雅些,村田笑笑不答。
芬芳说熟客太多,太早离场不妥,还是要多等一会,才能离场,村田慾火冲上了脑门,一直在傍催促爱子提早离场,好不容易,中场乐队休息,村田硬拉着她离开了舞厅,去到了赵姐的住处。
才进了门,村田迫不及待,就脱下了衣服上床,一支小型手鎗掉了出来,村田俯身检了起来,压在衣服上。
这次村田带来了新开发的人造橡胶如意袋,既薄又有弹性,使用起来舒服多了,科学还真能他妈的造福人群呀。。
村田还是那幺勇健,不在乎有血没有血,在暗红色的经血中进进出出,兴奋不已,爱子却感到意兴阑珊,勉强嬉笑奉承应对。